
经管之家App
让优质教育人人可得
立即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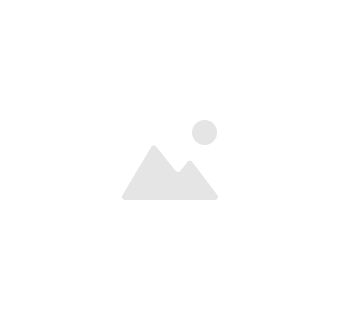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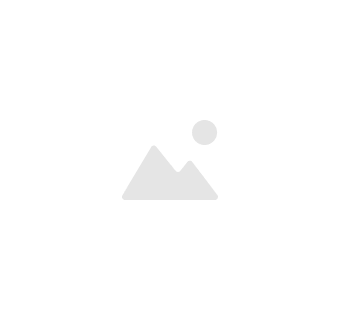
第一讲 我是谁
一、“人”是什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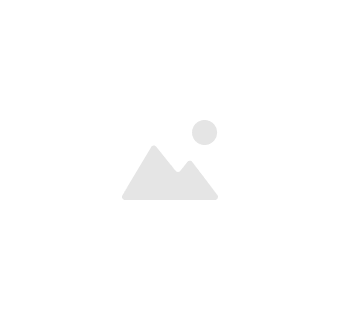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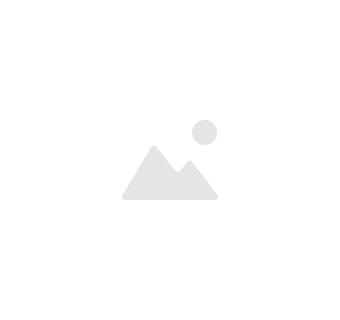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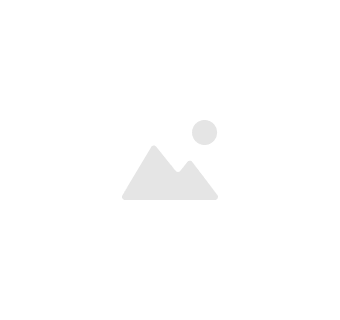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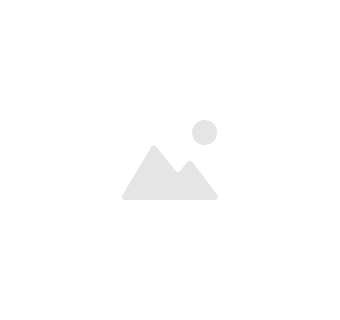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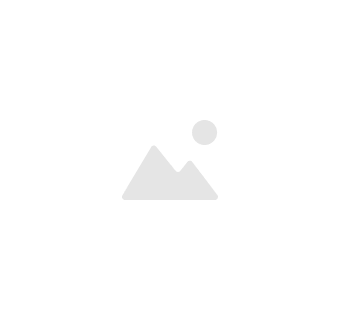
2、人怕人:进化的动力
根据进化论,任何动物都为了适应环境而不断进化着,但不同动物,进化的途径不同,动力也不同。只有人,不是靠体能,而是靠智慧在不断进化。
一个人可以跑得不如老虎那样快,也可以体格不如师子那样强,也可以力气不如大象大,甚至可以是不完整的人——比如缺胳膊少腿,缺眼睛少耳朵——但,只要他工具制造得好,他就可以杀死比他快的老虎,比他强的狮子,比他更有力的大象和所有其他肢体健全的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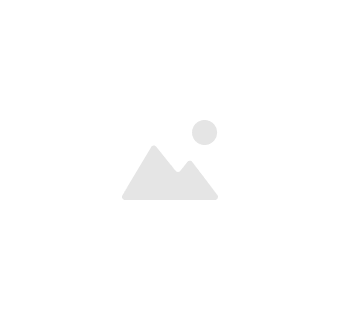
有工具,能杀死别的动物,人就有了安全感吗?
不,人还要怕——人自己!因为一个人有武器,别的人也会有武器。人能杀死别的动物,却要担心被别的人杀死,所以,人最怕的——就是人!
这种威胁最终使得人努力思考发明更好的工具,由此使自己更快、更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总是在寻求更好的、更快捷的、更强的工具杀自己的同类。从冷兵器到热兵器,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人类在武器方面的每次飞跃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制造石块到制造原子弹,人的行为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提升自己杀死同类或异类的能力,达到霸占更多资源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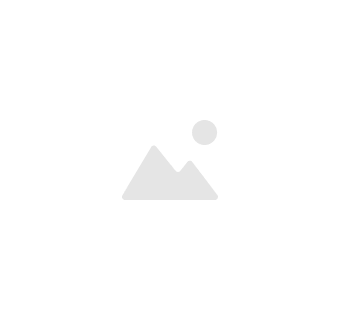
所以,对人来说,并不是体能上的“弱肉强食”,而是思维上的“弱肉强食”,谁更善于制造好的工具,特别是杀同类工具,谁就能生存。谁不善于制造工具,特别是杀同类工具,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就将被淘汰。
可见人怕人,促进了人智慧的增长,并进而促进了人的进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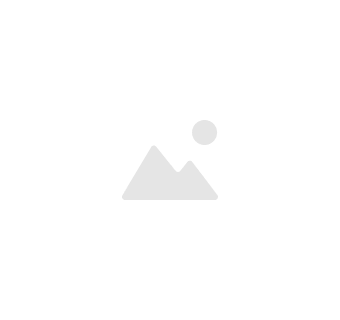
结论:
不能制造工具,或者尽管制造了工具但不善于利用,或者尽管善于利用工具,却不会用工具来杀动物,尤其不能杀自己的同类,这就是动物与人的区别。只要不会用工具杀自己的同类,动物就永远不是人,永远不会进一步进化成更高级的生命,而人——是能制造工具并利用工具杀动物的动物。
(待续)
二、人性的本质
认识自己,最深刻的莫过于认识自己的人性。自知者莫过于知己之人性,自胜者莫过于克服自己人性的弱点,抑制自己人性中潜在的恶念。

﹙一﹚、人的自然属性:
人的生物根性生命的自私,基因的自私与人的自私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自私性的基础却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固然,自私不必是恶,但在社会生活中也确难为善,不妨说自私是潜在为恶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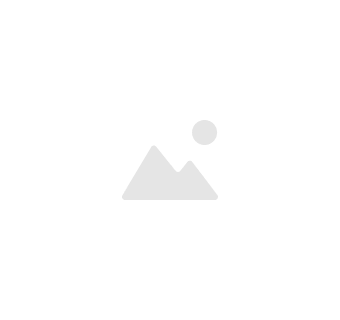
1、 人性的生物之根——元素
元素是世界的基石,元素组成了一切物质,包括生命!
人类最深层的自然之根是物质世界的最基本的原子结构,人类奇妙的对称形体等等,均源于原子波形的基本的对称属性。
人类次深层的自然之根是生命物体共同拥有的一套生命遗传密码,这使人不仅具有大自然的物质性,还同时具有不可摆脱的生物性。
人类浅层的自然之根是他作为人科动物的基因,基因在元素、分子、原子……和遗传密码的基础上为人类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生命功能。
总之,人类植根于物质世界、生命世界。人既是物质机器,又是植物、动物,但反之不然,物质机器、植物、动物不是人——而人必竟是人!物质元素、生命遗传密码和基因是人类的三层自然之根。
(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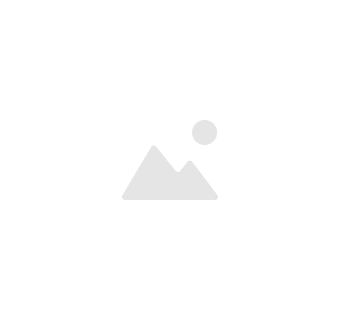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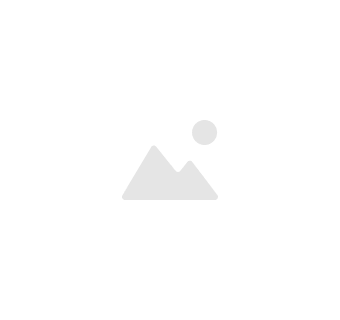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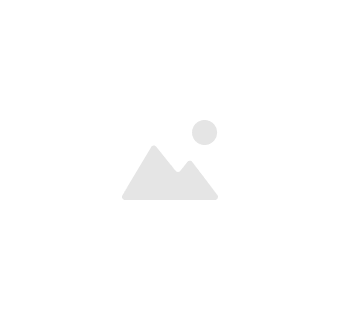
3、人性原欲与原恶——本能
人类的自然本性分其为生命本性和死亡本性两大类:生命本能又简称为人类的原欲,原欲有三:物欲、知欲和性欲;死亡本性又称为人类的原恶,原恶也有三:任性、懒惰和嫉妒。无能原欲或原恶,均为人类的绝对属性,在人类的生命存在中,这些属性虽然可以有所增减,却绝对不可能永远消失,除非人死了,一了百了。
人性原欲是人类生命意义之本,是衡量人性善的最基本的坐标,没有原欲——食欲、性欲、知欲,人类便不可能有追求善的原动力,但人性的原欲本身并不是善。
原欲之所以能为人类向善的动力,是因为原欲的满足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不食不得生,无性不得繁衍子孙,不求知不能趋利避害,然而只要人类动欲,便必露恶,即露出原恶——任性、懒惰、嫉妒。可以说,一切恶都根植于这三项原恶,就像一切颜色都可由红、黄、蓝三元色调配出来一样。
尽管三原恶都很直观,为明确之见,仍作定义如下:
任性——宁以无视既存社会法则﹙道义、道德、法律、制度等﹚的方式思想并行事。
懒惰——指望不劳动或少劳动而获得自己所需。
嫉妒——因别人某方面优于自己而对别人怀有恶意。
必须指出,仅作为心理状态而不诉诸行为,三项原恶本身不是恶,但它们是一切恶行为的心理根源。
显然,人性的原恶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不同,原罪是指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接受了毒蛇的诱惑,偷食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犯了最早的奸淫之罪。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有“万恶淫为首”的说法。古代西方人因原罪之说而推出人性本恶,其实没有多少道理,而且偷食智慧之果,以求得知识为恶反而与古希腊人的“知识即善”相悖。可见,古代西方人的人性本恶论虽然暗合人性偏恶的实际倾向,但并不表明他们对人类之恶真有完全的认识。
真正的人性之恶应该是人性的原恶。不能把原恶与原欲混同。原欲是人类必须获得满足生命意义的支柱,不仅不能说是恶,而且应该是衡量人性善的最基本的坐标,人类原欲得不到满足反倒是造恶的渊源。因此,中西方古人不约而同把淫——性欲的满足视为恶,而且是首恶、原罪,其实是不对的。淫不为恶,但淫起来不讲任何规矩、道德、法律而达到任性妄为的程度,就是十足的恶了。所以真正的恶不在淫,而在任性。人性的任性原恶一旦从潜在的可能性变成显在的社会行为,它便不是原恶,而是实恶了。
任性的本质是对人类社会中既存的一切规矩、道德、法律、诫条、制度……总之,一切行为“度”或“条规”的否定。这种否定不外乎两类:一是完全无知,二是明知故犯。在现实生活中,因任性的行为而作恶犯罪者比比皆是。因此,任性作为人性一项普遍的原恶是必须由社会和个人双方同时加以制约和防范的。社会的防范表现于社会权力的威慑,个人的防范则在于个人扩大求知的范围,其中包括对道德价值、法律责任、制度理性等各方面的认识。
懒惰的本质是对人类社会生存意义的否定,是对个人生活体验的拒绝。任何人在能够轻易获得原欲满足的场合都会任懒惰的人性原恶变成实际懒惰的实恶,尤其在在尚处于幼童的年代,由于长辈的娇宠,极易染上懒惰的恶习。懒惰似乎与任性不同,不触犯条规,而实际上懒惰之恶比任性之恶对人类自身更有害。实际上是一切恶行为的最深邃的祸因。贪污、偷盗、抢劫乃至杀人等罪恶无不深深扎根于懒惰之源,“万恶淫为首”实不如“万恶懒为最”来的确切、真实。
嫉妒的本质是对永恒、终极、自由的精神追求的缺失,来自竟争中的自私者内心的失落感。是对未来缺乏自信,缺乏希望的人经常的情感反映。他人的天赋、好运和成就通常都会引起人们这种内心的失落感。轻者艳羡,重则苦脑,过则涌现出对他人的恶意,再过者恶语伤人,再过则以恶行害人……因嫉妒而产生恶行为的事情非常普遍,几乎一切人都曾有过此类或轻或重的嫉妒和被嫉妒的体验和感受。
总之,原恶不等于已经是恶、或正作恶、或将一定要作恶,而是指人与生俱来即有作恶的潜在心理因素或动机。
人性原恶,从人的成长、进步的角度看,总之是人身上的一种根于自然的惰性,克服这些惰性即是人向人类的社会性,向人类的精神性,向人类的文明性跃升的起点。人类文明是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同时也是克制自身原恶使之不露形迹的过程。
结语:人生来即是一个多重的矛盾体,原欲与原恶,生命动力与死亡动力,知欲与任性,食欲与懒惰,性欲与嫉妒,更有它们交叉的互动,从而使得人性呈现出比魔方还要复杂万分的多变的生命属性。
(待续)
(二)、人的社会属性: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
人是自我运动的个体,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个体,人与人更是共同发展的个体。
人不断为了欲望的满足,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这活动的过程之中,必然相互发生联系,完全封闭的人是不存在的,只要是社会人就只有在联系的网络中才能生存……
1、人性的释放场
人性原欲与人性原恶是一个生命体的两面,它们是创造人类社会文明的原动力,又可称生命动力;一个是阻碍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原阻力,又可以称死亡动力。这两种力量都能在人类的社会状态中或付诸实现,或施以压力。社会是人性原欲获得满足的无穷无尽的源泉,社会同时也是帮助人类克服人性原恶的压力场,离开这个压力场,人类潜在的原恶就将变成显在的实恶。而人性的释放场之所以要分解为官场、市场和情场,完全源于人类释放和克制自己心理上的原恶的需要。
2、人性场之一:官场
——官场是人性任性原恶释放和制约的场所。
追求权力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动物的攻击性,雄性动物为争夺占有雌性动物群的“权力”而彼此角斗的习性,或许可以认为是人类追求权力本性的渊源。
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依附集群生活方式,而集群生活方式就需要权力,没有权力就将没有安全与和平。为什么?乃人性原恶所致。
一个人的人性原恶一旦从潜在变成实在,他即是个任性的人。任性的人是破坏既存秩序的人。任性的人彼此共处,要么相互反对引起战斗,要么相互联合结成更大的破坏性力量。仅仅靠分散的个人不可能制止、约束这种破坏性的力量。因此,为了共同的生存,必须要有更多人的联合。并按照一定章程、规则、契约、法律、制度……形成具有一定秩序的社会组织,各阶层的头领。这种组织可以按既存的条件拥有强有力的武器,推选出首领和各分组织,各阶层的头领。这种组织是一个具有暴力势能的
威摄力量集团(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可以对社会的任何未形成组织的个人构成强大的威摄力量。这种对任何人都具有强大威摄力量的社会势能场即是社会的权力场,也就是人性的官场。
﹡官场的基本功能:
稳定社会等级之间,人与人之间既定的秩序是官场的第一大功能;
保护和促进市场的发展是官场的第二大功能;
在情场的精神推动下,使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更进一步合乎人类既存文明(理性、正义、民主、自由……真、善、美)的需求是官场的第三大功能。
﹡但官场化也有陷阱:
最高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或根本就不受制约是官场的第一大陷阱;
权力私有是官场的第二大陷阱;
权力滥用是官场的第三大陷阱。
﹡官场的理性意识或公开宣扬的宗旨是公正、正义;是普遍地维护全社会,或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安全。
官场的非理性或潜意识则是损人利己,以人为壑,假公济私,以权谋私。
总之,人类社会权力空间的建立是人类离开自然状态的第一步。人类社会需要权力是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安宁与和平,需要起码的安全感。同时,权力关系的建立,也是为人类之间的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更是对人性原恶任性的制约。
(待续)
——市场是人们追求利益和对人性懒惰原恶的压迫场所。
追求利益(金钱),同样是人类的本性。动物为食物、巢穴而争斗的习性应是人类市场求利本性的渊源。
市场是人们追求利益的场所,是人们用自己的资本、物资、劳力、智力同自然、同他人进行自由交换的场所。任何人只有通过这种自由自愿的交换才能获得为生存所需要的物资,金钱。人类之所以需要市场,同样是因为要制约人性中的懒惰原恶。
处于自然中的人,任何人都有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懒惰的原恶倾向。人类的懒惰恶习固然有害于社会,实质上更有害于自身。因为人的智慧、才干、创造与勤奋密不可分,懒惰的人空徒减少社会的生存物资不算,更造就愚味、无知、无用的个人自身,从而实际有害于个人兼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市场正是通过压迫人性懒惰的原恶,来使人类社会获得和保持实践的意志和生存的活力。
﹡市场的社会功能:
以高效益为社会增长财富,以满足社会全体人们的生存需要是市场的第一大功能;
受官场的法制,从官场的威摄力量中取得和平、安定的保证,并以其经济力量的反缋,而对官场活动回加相应的制约是市场的第二大功能;
用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力量支持人类情场活动,避免官场对情场的专制垄断是市场的第三大功能。
﹡市场化陷阱:
金钱(资本)变成权力,贫富两极分化是市场的第一大陷阱;
人的精神空虚,除了金钱,即是人们赤裸裸的欲望的满足,及时行乐是市场的第二大陷阱;
金钱的滥用使人类变本加厉地放纵人性的原恶,而不是对其自觉的制约是市场的第三大陷阱;
﹡人类真正需要的市场宗旨:
第一是尽量公平地供给社会中一切人最基本需求的物资,公平的原则是劳动创造的原则。
第二是尽量普遍地、平等地压迫社会中一切人的懒惰的人性原恶。
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形成官场是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第一步,那么,人类社会的形成市场是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第二步,也可以说是人类真正变成社会性动物的重要完成的一步。
第一步是在寻求安宁与和平的生存,第二步则在寻求合作与稳定的生存。第一步在普遍地抑制人性的任性原恶,给人类的自私找第一个来自社会的合适的有利于社会安全的制动阀,第二步则普遍地抑制人性的懒惰的原恶,为人类的自私找到一个来自社会的合适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刺击阀。在铁面无情的市场中,人们不能不激励自己勤奋工作,用自己付出的劳动换得基本的生活需求的物资或金钱。
(待续)
——情场是人类追求人的情感本性对人性嫉妒原恶消解的场所。
情场是人类追求情感的场所。动物的性本能和利他行为以及同类不相食的本能可能是人类追求情感的本性的某种渊源。
人类有崇拜仁慈、万能的神的宗教信仰,有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有对人与人之间好意、友谊、情爱的欢娱的眷恋,这里的信仰、认识、眷恋均可分别看作对神、对自然、对社会和他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构成了人类在文明历史长河中客观上取得进步的“文明”标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了这些情感,而仅有权力和金钱,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其实没有两样,或许还更坏。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更坏的时刻。人类的尔虞我诈,自相残杀,对人的迫害、虐待的确比某些动物对待同类还不如。
可见,人类的情感是人在与神、自然、社会、他人的交往中所获得的某种心灵的安抚(当然,也包括安抚的反面:不安、焦虑、恐惧)。人类的信仰、知识、眷恋即是这种“安抚”的过程,也是这种“安抚”的产物,因此也即是情感追求的自身。
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情场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类自身人性的原恶——嫉妒。具有嫉妒原恶的人类只有在人性情场的活动中才能消解因嫉妒而生的恶意,开拓心胸获得创造性直觉灵感。一个人的嫉妒的原恶一旦从潜在变成实在,即是一个嫉妒的人。嫉妒的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绝望的情绪,并使这种情绪转化为对别人的恨恶,甚至有意或无意作出伤害他人的言行举止。
人类的情场活动追求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普遍的情感。人们通过宗教信仰、科学研究、学术讨论、友好交往以及同异性的情爱等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追求、超越权力和金钱的人类情感。这种情感贯通宇宙的永恒、人性的自由、隽永的情爱,人类的灵魂在这种情感中自觉获得真、善、美的洗礼、净化和再生,获得人性直觉的创造性灵感。
心向望永恒的人不是不会嫉妒,而是没有时间去嫉妒,生命的促迫不容他自寻烦脑;心向望自由的人心眼直视天边的飞鸿,蓬间麻雀的闹声干扰不了他心中的视线;心向往精神之爱的人,最令他销魂的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直视、坦诚及交融……
一个嫉妒的人让绝望的情绪困扰自己,用有毒的箭矛伤害他人,不过是一个懦夫,一个侏懦,一个让自己的渺小压垮的人。人们因权力、金钱、美女而起的嫉妒均可以在情场的积圾追求的活动中得到有效的消解。顽强而专注的精神追求本身即是一剂医治心灵创痛的良药。而对真理、道德、信仰、审美修养等等不断高层次的追求,则是保持人生自信、杜绝嫉妒原恶,高扬人性审美价值的最佳途径。
﹡情场的社会功能:
情场的社会功能之一在于为人类提供创造性的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真、善、美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以此为社会中全体人类指明社会进步的方向和人格升华的尺度。
情场的社会功能之二为促进官场的理性(正义),弱化人类追求权力的本性,增进社会中一切人对自身正当权利的意识,激起人们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行合理斗争的勇气和热情,以便以安全的社会脉动取代令人恐惧的社会暴力。
情场的社会功能之三是向市场回供信仰、智慧、情感方面的新信息,有选择地放大、扩张基于市场的人性原动力,不使追求金钱的人类本性过份膨胀,以此推进人类整体的文明和幸福。
﹡情场化的陷阱:
情场的第一大陷阱表现在情感的权力化;
情场的第二大陷阱表现在情感的金钱化,或情感的市场化;
情场社会的第三大陷阱是科学主义。
﹡情场的理性意识是坚持科学认识的法则,反对迷信、盲从,坚持对一切抽象观念的逻辑证明和实践证明;
情场的非理性意识则是对动物性、人性以及神性的交感,总之是对生命自身的直觉;
神学、哲学和科学是对人类情场活动历史性条理的反映;
知识教育、道德习俗、宗教礼仪是人类情场体验的不断再现;
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活动以及新闻媒体则是人类情场指向未来的表现活动。
可见,建立情场,营造情感观念以及真、善、美的精神形态,是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第三步,也是人类最终走出动物的自然性的重要的一步,更是人类真正进入社会文明状态的最本质的一步,它使人类真正具有了自我发展的主动的精神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认定:一切人类的文明史,本质上都应是人类社会情场的发展史。
(待续)
(三)、人的精神属性:人的思维关系的属性那么,从什么时侯开始,人类才真正显得具有了人类的精神性呢?公元前500年左右到公元初年前后这大约500年中,人类竟是那么神奇地几乎同时地在亚州的东方和西方怒放了人类伟大精神性的花朵,而且具有确凿的人物成为这些精神花朵的摧放者、代表者。它们是: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爱的精神;古希伯来人的伟大先知、古希腊的伟大哲人和古代中国的伟大圣人。
什么是人类的精神性?人类的精神性即人类向善的意志,是人类处于社会生活中受到共同的人性原恶的困扰时必然向善的渴望和追求。
在人类没有精神性,或者精神性尚处于完全不被知觉的阶段,人类的生命与动物其实没有区别。人类完全不为已经过去的活动的挫败、希望的丧失,情感的断绝而痛苦,而焦虑,而哀伤,这时的人类,只要有吃的,能避寒,能避野兽的攻击,他就能安之若素地生存。可是,当人类一旦自觉有了精神性,有了对恶的恐惧,有了对善的向往,有了信仰,有了认识,有了爱的依恋,……这时人们的悔恨、希望和志在必得的决心等等便成了人类生活中既制造活力,又制造痛苦的大善大恶的生命意义之源,这也便是人类的精神性有了知觉、认识之源。只有人类才有知识、有思想、有认识,
可见,精神性是人类特有的属性,更确切说:精神性是文明人类特有的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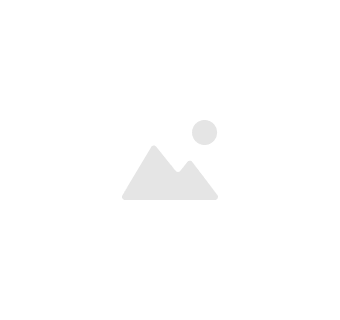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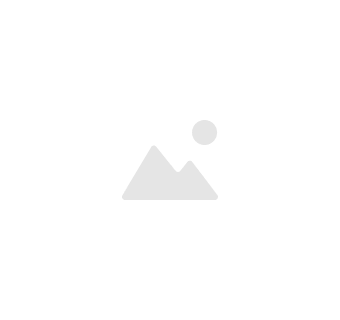

古希腊人是人类元精神之一,即求知精神的发现者和首创者。因为他们最早确认了“善即知识”这一伟大的命题,而且在具体的求知的思想探索方面作出了伟大的榜样。他们首先确定了逻辑思维的形式,发明了概念的定义,创造了推进思维的辫证法,首先对自然问题提供了抽象分析的思考……等等。
什么是求知精神?人类的求知精神是以人自身万物的尺度,也即以人的生存、温饱、发展总之福利与幸福的需求为尺度对人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加以旨在求得一个终极的和谐的目标的洞察。因为目标是无止境的,所以这种洞察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
“善即知识”这个命题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来的。苏格拉底认为,人要向善要想有德性,就必须先“认识你自己”,“如果你丢弃知识、你就不会在任何其他事物中找到幸福的王冠”,知识就意味着“善的本质”。
“事物善或恶的程度取决于它们是否处于知识的导引之下”,“智慧是惟一的善,无知是惟一的恶,其他都无关紧要,难道这不是最终结果吗?” 苏格拉底认为重要的是在确定真理,“问题不在于说这些话的是谁,而在于它们到底是真是假。”在这里,显然苏格拉底把“真”看成了“善”的前提,只有确定了真理,才可能进一步作出善恶的判断。求得知识真理的过程本身即在求善,因此,善即知识。苏格拉底首先把求知的理论问题当着求善的核心问题。不管这个命题本身完备与否,就象古希伯来人先知把善界定为上帝的信仰一样,苏格拉底以及其它古希腊哲人则把人们的向善的意志引向了对终极、和谐的知识的追求,从而启迪了人类求知精神。
在市场化社会条件下的人类求知精神对于克服人类身上的懒惰原恶来说,是一种极可贵的人类精神,同样是一种极有针对性的人类进行自我控制的向善的意志。英语民族首先获得这种精神和意志,所以人类的近代文明的新的突破和跃进是由他们首先开始的。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最早在英国发生。
信仰精神的本质在于永恒、惟一的真;求知精神的本质为终极、和谐的善。从历史上看,真先后善,真是善的前提,无真不善,这也是苏格拉底“善即知识”命题的推广,求真是达到善的必经之途,求知是向善的迈进,没有真便不可能有善。
求知精神如同科学精神一样,其精髓是——不迷信、不空洞、不满足。
(待续)
3、 中国圣人与仁爱精神
古代中国圣人孔子是人类元精神之一,即爱人精神的发现者和首创者。他最先提倡“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矣”……在全人类的古代文化中,提出“爱人”达到如此思想境界者,孔子是第一人。
人类之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母爱:第二类是性爱;第三类是博爱,即爱人。母爱纯属自然之爱,是动物也普遍具备的爱;性爱虽然也属于自然之爱,同样也为动物所普遍具备,但对于人类来说,它却是社会性的开端;博爱纯为社会之爱,爱父母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是最基本的社会或文化的爱。
孔子看到了孝是仁爱的基础(仁之本),是培养人类真诚精神不可缺的过程,因而把爱人之精神落实到孝悌忠恕上,尤其重“孝”。 “仁”是孔子最高的善,“仁者爱人”,而且更有“孝悌为之本”,而实行孝悌的根本的心理方法在“恕”,“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将心比心”且忠恕之道,夫子“以一贯之”。孔子以一贯之的正是爱人的精神,且集中于行孝。
“孝”就是爱父母,爱父母是爱人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社会之爱。而家庭正是社会的最小单位——细胞。正是在家庭之中,儿童经过爱父母的训练,学会了爱,主要应该是学会了和训练了爱的能力,即服从理性的能力,勤奋实践的能力和思维创新的能力。那些只知道接受父母的爱却不知爱父母的人,那些从小娇生惯养缺乏爱的能力训练的人,他们会终生不懂得爱人。一个不懂得如何爱人的人,也终生不可能真被人爱。可见,爱父母正是让爱的能力逐渐成长的过程,父母既是儿女爱的对象,也是教会儿女爱的能力的重要的导师。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伟大的爱人精神,竟逐渐演变为儒家治世经国的中心思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在于忠、恕,齐家在于仁、孝,忠孝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它要求人们把血缘型利他情感活动扩而大之,以至上对君主,下对庶民,君是父君,民是子民。凡入朝做官的人都必须视君若父,爱民如子。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天下达到大治。这尽管是儒家的乌托帮,却以一贯之两千多年。
古代中国圣人创造了伟大的爱人元精神,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它常以一种基础的形态——孝悌精神呈现。但他们使人类把人类的爱,特别是把对父母的爱变成人类向善的意志和行为,使它成为一种伟大而真实的文明精神力量。
爱人精神之所以是人类的元精神,是人类一切精神的基础?是因为爱是人类幸福的支点,是一切精神价值的支点,如同信仰是“真”的源泉,求知是“善”的源泉,爱人是一切“美”的源泉!
(待续)
三、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1、圣哲论善恶
人性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无论中外,自古以来的圣哲多只以善恶来加以判别,并不曾更具体指称人性是什么。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或人性既非本善,亦非本恶。
中国古代儒家圣人基本上是人性本善观点的代表者,其中尤以孟子的表达最为明确:“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更具体定义善即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孔子虽未明确说过人性本善或本恶,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孔子对善的最重要的解释:“仁”,却透出了人性本善的倾向:“克己复礼为仁”,“仁者人也”,而且更有“为仁由己”之说。正因此才有相传宋代王应麟《三字经》的总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大体说来,这四句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孔孟儒学的人性论观点的。孔孟的这种人性论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
与中国古代圣人相反,西方古代哲人,尤其古代宗教先知是明确的人性本恶论观点的代表者。西方人喜欢称他们的文化源自“二希”的传统。所渭“二希”即指古希腊与古希伯来。
古希伯来人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宗教信仰传统。古希伯来人的宗教——犹太教以及犹太教的变种基督教,尤其后者,在近两千年的时期里,一直是西方人主要的精神支柱,基督教人性本恶的观点普遍为西方人所接受。基督教主张原罪说,即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先天地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偷食了智慧之果,懂得了男女羞耻之事。基督教原罪的观点在西方近代宗教改革的新教领袖——路德·加尔文那里更是获得极端的发挥,他们索性明指,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
古希腊人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哲学传统。古希腊人虽未有明确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但苏格拉底定义的“善即知识”的观点却是贯穿古希腊哲学的传统观点。而“善即知识”的观点本身即已经具有人性本恶的倾向:既然知识不是与生俱来,所以人生来无知,无知即不善,不善即有恶的偏向。
以此看来,说西方人有人性本恶论的传统倾向,决不为过。
尽管在人性本善与本恶的观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相反的传统偏向,但在关于人类有向善的必然性的认识上,或向善的乐观态度上,中国圣人与西方哲人和宗教先知却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圣人主张道德修养,内求向善;古希腊哲人主张增长知识,古希伯来宗教先知主张信仰上帝,二者均属外求向善。
中国圣人与西方哲人在关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观点上的传统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极其不同的发展的命运。
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认识:阻碍一个人进步的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这个人自己。同样,阻碍一个文化发展的最大的敌人,往往也是这个文化自身。原因何在?即在于人们常常都缺乏对自身的正确认识。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中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可以认为是一句天启式的格言。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即以这句格言作为自己终生的警醒剂;中国古代的智者老子也曾讲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认识自己,最深刻地莫过于认识自己的人性。自知者莫过于知己之人性,自胜者莫过于克服自己人性的弱点、抑制自己人性中潜在的恶念。
(待续)
人性在本来不可分的意义上统合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层属性。三者本不可分而我们强分之,其目的不过在有利于理解人性。在分作以上三层的基础上,我们再作善恶的思考和判别,无论是中国古代圣人关于性本善,还是西方哲人关于性本恶的界定,我们都可以大体有如下的结论:
1、人性的第一层,生物性:偏于恶;
2、人性的第二层,社会性:善恶交错;
3、人性的第三层,精神性:偏于善。
很多圣哲追求人性的精神性,由此宣传人性本善;
不少先哲强调人性的生物性,由此宣传人性本恶;
有的哲人看到了人性的社会性,所以提出善恶并存的观点;
还有的哲人则研究人的利己与利他,进而发现这一切来自动物生存的本能,因而得出“无善恶”的结论。
……
对于上面的分析及结论,估计多数的读者会给予赞同的,但人们肯定会问,上面的结论对于推论总的人性是善或者是恶有什么用呢?全部三层来一个三一三十一,取算平均值,还不是善恶难辨!
对于这个问题我推荐一条带有假设性的公理,即:愈是出现得早的事物,它的惰性愈大,也即它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或能动性愈小,而且这种惰性与它出现至今的时间成正比。
用这条公理来判断人的惰性,且用上面三个层次来分别判断,即有如下结论:
1、人的生物属性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原生质,也即生命的起源,距今至少20亿年;
2、人的社会生物属性出现的时间,最多可追溯到三叶虫的起源,距今大约5亿年;
3、人类作为精神性动物出现的时间,最多可追溯到智人的出现,距今恐怕也只有不到200万年。
按照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大致算出三者所具惰性的比例:
生物惰性:社会惰性:精神惰性
﹦20×10的8次方:5×10的8次方:2×10的6次方
﹦2×10的3次方:5×10的2次方:2
如果以人性的总惰性为1,则其在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的惰性比例将可换成下式:
生物惰性:社会惰性:精神惰性
﹦0.8:0.2:0
以此来计算人性的善恶偏向的分配:
0.8(恶)+0.2(恶+1/2+ 善1/2)+0(善)
﹦0.9(恶)+0.1(善)。
结论是:人性的90﹪偏向恶;
人性的10﹪偏向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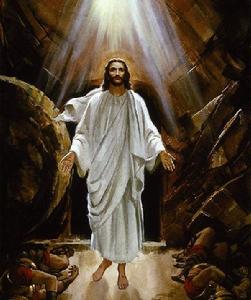
这便是对人性善恶倾向的总估计,正是因此,我们说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对人姓善恶的判别是符合真实的人性的。相反,中国古代圣人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不符合真实的人性的。中国古代圣人带头在“认识你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始终处于某种自相矛盾的境地。
在中国古代甚至迄今,说人性本恶,或人生来自私,是决不受欢迎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更喜欢孟子而不太喜欢荀子的原因。扬朱说“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从人性的本源(并非人性的精神)说,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然而两千多年来不仅此论令人厌恶,连带扬朱本人也不知遭人多少唾骂。墨子的“兼爱”,扬子的“为我”,孟子便曾一道斥之“无父”,“无君”,是谓“禽兽”。……
很可能,读者对前面关于人性善恶偏向的估算会不以为然。的确,“计算”善恶从一个假设的公理出发,其结果必难以服人。但并不是毫无根据——生命的自私,基因的自私与人的自私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自私性的基础却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固然,自私不必是恶,但在社会生活中也确难为善,不妨说自私是潜在为恶的基础。只是因为社会生存对于合作的需求迫使人们不能不追求善的价值。不论这种善是中国圣人所谓的克己、礼让、孝娣、忠恕,还是西方哲人的求知或者宗教先知的信仰上帝。不管怎么说,善的追求是随着人类的社会生活的需求而产生的,没有社会生活的需求也就没有善,也不必追求善。提高善的成就水准的还在人的精神性,也即人类对自然、社会、他人、自身,尤其对自身的人性的知性的洞察。在这方面,不能不承认,苏格拉底定义“知识即善”的确比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更富有远见。
总之,人性确有恶的倾向,从人的成长、进步的角度看,这种恶的倾向总之是人身上的一种根于自然的惰性,克服这些惰性即是人向人类的社会性,向人类的精神性,向人类的文明性跃升的起点。人类文明是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同时也是克制自身原恶使之不露形迹的过程。
那么,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请同学们听第二讲——我从哪里来?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收藏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