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瓦氏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着货币商品及生产要素的供需全部均衡(英文GENERAL既有“一般”也有“全部”的含义,在此,应该理解成“全部”为妥)。而且他认定,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之上的他的理论,是该市场的最优状态:这时候,消费者达到效用最大化,商品生产成本最低,生产要素达到充分就业,企业达到利润最大化。
2,我认为,纵使在瓦氏所强调的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他的原义上的一般均衡也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伟大发现。他的证明也是错误的,建立在逻辑前提和推理错误的基础上。他和马克思所犯的错误非常相似:在此我不再详谈。尽管有许多学者因证明瓦氏理论的存在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如诺奖),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3,如果瓦氏正确,则和凯恩斯的观点不相容:凯氏已经证明,完全竞争下的市场经济,不能达到充分就业。我认为凯氏的观点无懈可击。
4,我并不象那些非此即彼的人们断定的那样,认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学术价值:我认为瓦氏的理论,有很高的启示价值,如果我们设定一个社会伦理观认可的“一般均衡”的标准,然后向这个方向努力,这不是很有经济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吗。比如说,凯恩斯,他以特定社会伦理认可的劳动力就业标准,作为“充分就业”的标准,然后研究这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作出的非常大的学术成就。
以下转帖自CENET:
7月7日是小凯的忌日,我要写一些文字来纪念他。
前不久读到田国强教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此文在教导学生如何做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对小凯开创的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不仅如此,田教授还在各种场合高调批评小凯的理论。我对田教授素有敬仰,且对于公开的回应本也毫无兴趣。但是,小凯已无法开口做任何辩白,而不少人对经济学纯理论领域的批评恐又无足够的鉴别能力,田教授的文章和言论因而对小凯的理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随着小凯忌日的来临,我需要站出来替他澄清。否则,我的内心无法面对小凯。
田教授是这样批评小凯的——
“从以上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的讨论可以看出,经济学中每一个理论或一个模型都是由一组关于经济环境、行为方式,制度安排的前提假设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所组成的。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越一般化,理论的作用和指导意义就会越大。如果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太强,它就没有一般性,这样的理论也就没有什么用处。这样,成为一个好的理论的必要条件就是它要有一般性,越具有一般性,解释能力就会越强,就越有用。一般均衡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在非常一般的偏好关系及生产技术条件下,证明了竞争均衡存在并且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笔者之所以在2002年所编的《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的前言介绍中批评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就在于在他理论框架下所定义一般均衡模型需要施加一些非常不现实的假设,而不像一般均衡理论那样能在非常一般和现实的条件下成立。小凯等人在证明均衡存在性定理、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以及核和均衡集等价定理时都用到一个假定:决策人集合是无穷不可数的。对有限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经济环境来讲,一般均衡解一般不存在。它只对个别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参数都要具体给定)
诺奖得主Aumann教授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新古典瓦尔拉斯经济学。在此方面,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上面提到的1964年文章中关于“连续统”经济中的核等价理论(theory
至于田教授所说的“它只对个别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参数都要具体给定)
田教授在对小凯进行上述批评之前,看来没有仔细读过小凯的著作,也谈不上对小凯理论前沿发展的了解。这个判断是基于以下两个事实。第一,田教授现在对小凯的批评,其实部分地只是在重复十多年前一些审稿人的批评。但是,当上述三篇文章完成之后,在主要的纯理论界就不再有此类批评的声音。田教授的批评,还有部分地则是因为自己忽略了完全竞争模型的基本假定而引起。小凯在“超边际经济学近期文献综述”(2001)一文中,以及同Milgrom的讨论中(参见《杨小凯谈经济》一书)回应道,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现在,所有的审稿人对此已无异议。第二,田教授在其文章中说,“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包括钱颖一、林毅夫及笔者本人,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作(做)过一些讨论。但谈及分析框架的,笔者只见到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其实,田教授文章中要正面表达的核心内容,小凯多年前早就说过,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比如,1998年中文版《经济学》的导论部分,2000年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第1章,2003年中文版《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分析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两本教科书的导论部分,以及2004年《杨小凯谈经济》一书中收录的文章。小凯的这些思想,很多年轻学生都耳熟能详。田教授没有提及小凯上述任何著作,说明他对小凯的思想其实并不太了解。
我相信田教授之所以这样批评小凯的理论,主观上并不是出于要故意贬低小凯,而是因为田教授以为自己的批评是成立的。在对小凯的理论进行否定后,田教授还回忆起他同小凯的友谊。但是,这在客观上可能会对不明就里的读者产生更大的误导——
“[10]需要指出的是,我批评小凯的超边际分析中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不表示我不欣赏小凯的学识和人品。相反,我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学问、具有非凡道德勇气、正直、敢于说真话的、具有中国典型士大夫气质的一代学人。我和他相识22年,与他的私交也不错,他喜欢和我讨论他的经济理论,我也不时对他的理论给出我的看法和批评,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四个月,我和他及他夫人小娟交往较多,主要是为小凯联系来美治病及住宿的事,我还历历在目2004年6月21日从中国飞达美国芝加哥机场最后一次和小凯通电话的时候,可能我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最后与他通话的人。想不到,17天后,小凯于2004年7月7日去世,实在让人痛惜!”
说到友谊,我知道小凯一家对田教授是有真情义的。小凯去世后的那年冬天,小娟带着孩子巡游香港、日本和大陆,目的是为了拜访小凯的生前好友和学生,答谢他们对小凯生前的关爱。小娟母子俩在我家度过了2004年的平安夜,同我们说,不知道以后孤儿寡母地何时才能回大陆。之后他们赶往上海,为了去看望小凯生前的朋友,包括田国强教授。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送他们到车站的情景。我先是不过脑子地开车将他们送到北京西站,但到检票厅时才突然意识到,开往上海的列车应该是在北京站。我们一下子着了急,因为离开车时间已不到一小时,而当时正是北京下班的高峰。为了赶时间,我们只得拖着大包小包挤乘公交,因为公交车可以走公交专用道。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狼狈不堪地在火车离开前一刻赶到北京站。后来小娟打来电话,说在上海见到了老朋友田国强教授,终于了却了小凯的心愿,真是十分地高兴!云云。
作为小凯生前好友的田教授,想必也知道小凯生前在西方主流学术圈的艰难。小凯生前曾对我抱怨,一些长期接受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人,其思维总是摆不开旧的框框,难以接受新的思想。他同他们之间有时候非常难以沟通。他对此很是无奈。但是,对于真正有见地的批评,他从来是认真对待的。他不会因为这一理论是由自己一手开创,就讳疾忌医地将这些批评和建议拒之门外。实际上,小凯的学说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正是在众多匿名审稿人有见地的批评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无论如何,这个由华人独立开创的经济学体系能够得到发展和完善,都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小凯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开始赢得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只可惜,小凯在他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英年早逝。小凯为他钟爱的理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Buchanan)在悼念小凯的文章中说,“杨小凯于2004年7月7日不幸逝世,经济学界丧失了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本人对杨教授之推崇,下述事实可作为最佳佐证:最近连续两年(2002年与2003年)
在上帝的国度,小凯的灵魂已经安息。我们怀念小凯。而怀念小凯的最佳方式,正如布坎南所说,乃是“由散布世界各地的学术同行们进一步扩展、深化及应用其基本洞见。”
2006年7月2日写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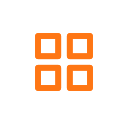 全部版块
全部版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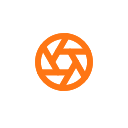 我的主页
我的主页

 收藏
收藏





 [em01][em01]
[em01][em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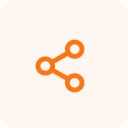
 加微信,拉你入群
加微信,拉你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