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17-895867.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黎在珣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
部分国人和宣传部门又有开心事了。
你们常说中国学术造假问题严重,你看,你看看,哥伦比亚大学这样世界一流高等学府里的著名学者不也造假了?现在总该清醒清醒了吧,外国的月亮不会比中国的月亮圆。
我们完全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存在的问题美国一样存在。中国有腐败,美国也有腐败。中国有穷人,美国也有穷人。……
总是盯着自己所谓“丑”的国人啊,抬起你们的头,挺起你们的胸,昂首阔步向前走吧。
(观察者网讯 编译/刘旭爽)2015年5月月底,美国学术界曝出一个几年不遇的大丑闻:一名加州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上的论文,被发现涉及数据抄袭与作假。而涉事论文的合作者,则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有名的政治学教授。
这桩学术造假不但性质匪夷所思,被捅破的方式也极不同寻常:如果不是一个博士生缺钱做毕业论文的数据调查,也许永远都没人去质疑它的真假。
大卫·布罗克曼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的博士生,2013年时还在上三年级。同年9月他读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迈克尔·拉科的一些文章,深感佩服。拉科当时是政治学系的研究生。两人在美国政治学会举办的年会上(芝加哥)碰面,拉科向布罗克曼展示了自己的一些初步研究结果。
这些研究成果相当了不起,任何看过的人都认为它们会轰动学术界。布罗克曼也不例外。拉科的研究里有一个环节是让拉票人去加利福尼亚州选民家里游说。他在调查报告里写道,拉票人先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然后以此为前提同选民就婚姻平等问题展开简短的讨论——这会深刻影响到选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拉科这个结论是通过谈话前后进行的在线调查得出的,他还告诉布罗克曼,他计划让一个大人物也参与到这个研究里——唐纳德·格林。后者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声望很高的政治学教授,也是布罗克曼在耶鲁大学的本科论文导师。
拉科的研究结果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部分在于它们挑战了几乎所有的已存政治信条。过去的研究报告显示,政治游说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影响到选民的决定,而拉科的调查结果则表明事实并不如此。先前的无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同等条件下,人类总是会坚守自己的政治信念,即便他们的信念在劝说下稍稍有了动摇,一当他们发现游说者的企图,就极可能扳回自己的立场。但拉科却发现这并不是广泛适用的:他就人们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作了先后比较,发现人们的前后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会持续数月的时间。
2014年12月,拉科和格林的研究报告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大轰动。这篇题为“当接触改变思想:一种传播同性恋平等权的表达方式”的文章引起了《纽约时报》和《美国生活》(观察者网注: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档每周一次的广播节目)的关注。它还迫使许多研究者改写了自己的课题,改变了游说者与赞助商的拉票方式,并且激发了一系列的后续调查。
布罗克曼在看到拉科的研究成果后十分动心,想展开同样性质的调查,即,自己寻找拉票人,自己制作调查样本。他面临的首先是预算问题。他做了大致估算:拉科的调查需要的拉票人是一万,每个人的报酬是100美元。也就是说,展开这样一项研究需要100万美金。疑点就在这里,拉科只是个研究生而已,除非他自己财力丰厚,否则根本无力进行这个课题。布罗克曼给许多民意调查公司发去一份咨询提案,得到的大部分回复都一样:它们也没有能力来做这样一项调查,何况是一个研究生?那么,拉科是怎么做到的?
上个月下旬,布罗克曼和他的朋友乔希·卡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还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家彼得·阿罗瑙公开发表了一份长达27页的报告,逐条指出了拉科与格林那篇文章存在的许多“谬误”。“谬误”是个客气的字眼,事实上,这份报告揭露了一个严重的事实:拉科根本没有做过任何的调查,他声称同一家名为uSamp的调查公司有过合作,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明。实际上,拉科的做法很简单,他先找来一份早已存在的数据,再把这数据据为己有,伪造出那种充满说服力的“效果”。这种数据造假近乎无耻,很少有人敢这么做,而敢在《科学》这样的杂志上造假,称得上胆大包天。拉科的合作者格林第一时间致信杂志,要求把文章撤下,而《科学》杂志在未征询拉科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应允了这个要求。拉科已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份工作,预定会在6月份正式入职,目前他拒绝回应媒体,并且试图修改他简历中的不实之处。
但在布罗克曼、卡拉还有阿罗瑙公布他们的报告之前,有人就对拉科的数据表示了怀疑。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乔恩·克劳斯涅克说直到《美国生活》的制作人联系他之前,他都没有听说过拉科的研究,他认为这项研究听起来不可行,但当他看到这篇报告的合作者有格林时,就打消了疑虑。《我们的科学》(Science of Us)杂志致信格林,格林承认自己没有尽到监督责任:“我无地自容,我从没想过数据的真实性问题。”
不止克劳斯涅克一个,学术界和媒体都把拉科的研究结果视作真理,尽管它们看起来就显得不可思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格林名声在外,大家看到他本人是这份报告的合作者,自然就相信了。而另一方面则是,不论是学者、记者还是社会活动者都倾向于相信拉科的调查结果。这是个雪球效应:这项报告影响越大,相信它的人就越多。
拉科投给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份简历(它也是在网上公开的)里也包含了大量的虚假信息:他列举了自己进行过的项目,这些项目总计需要79.3万美元的赞助——一个政治学研究生根本就拿不到如此多的资助。他还伪造了一份教学成果奖。拉科的许多虚假信息(包括那份研究报告里的数据)多年来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但直到布罗克曼他们公布那份报告以前,没人想到去质疑这些东西的真假。格林在这一丑闻曝光后说:“我不明白的是,他在对数据造假之前就应该清楚,如果有同行想重复他的研究,他们会发现根本不可行,真相也就暴露了。……既然如此,干嘛不老老实实做研究?”

涉及数据作假的拉科
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人们才发现真相?这样一个丑闻对美国学术界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科学》杂志采访了布罗克曼,在三个多小时的谈话里,布罗克曼向记者原原本本讲述了这整个事件。
布罗克曼认为,他的经验可以给学术界敲上一记警钟:以政治学界为例,它并不鼓励青年学人对同行进行质疑。在他展开这项调查时曾多次受到朋友以及导师们的告诫,他们告诉他不要继续下去,除非他想以“闹事者”的身份出名,或者被人讥笑为自己没有创意,专挑别人研究成果的刺。
2013年12月时,布罗克曼正准备展开同拉科一样的调查,所以他也咨询了uSamp,就是那家拉科称同自己有合作关系的数据公司。布罗克曼并未提及拉科的名字,只是询问该如何进行此类调查,对方称没有做过这样一类调查,也许不能胜任。
接下去布罗克曼向许多其它的调查公司发去了提案,但得到的回复差不多,它们都认为,类似拉科的研究报告里所提到的那种调查规模太大,它们无力进行。布罗克曼说他当时起了疑心,因为按拉科的情况看来,uSamp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调查。
2014年秋天,卡拉加入了布罗克曼的项目,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布罗克曼看到了拉科的原始数据(他读到了那篇还在审查中的研究报告)。他很快就发现不对头的地方:一份大规模调查样本的数据是不大可能这样井井有条的。光从数据来看并不能发现有什么漏误,但显然它们缺少进一步的支持。这时布罗克曼的心里开始有了底。
布罗克曼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师友,大多数人提醒了他两件事:第一,除非他有合理的证据,否则就不能贸然提出怀疑。这会影响格林的声誉,也会影响到正在起步的拉科的学术生涯;第二,即便数据真的有猫腻,布罗克曼也不该冒险当出头鸟。
对于一个前途未定的青年学者来说,这些劝告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当你公开质疑某人的研究成果时,你不可避免会陷入麻烦。如果那人比你有声望,比如说格林,那你就是在嫉妒,在炒作;如果那人与你地位相当,那你就是在排挤同行,并且枉费心机。要知道,在学术界这个小圈子里,所有人都知道彼此的研究方向,也许那个你攻击的人,正是评估你毕业论文的人。再者,学者的声望是靠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攒起来的,质疑旁人的研究成果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因此布罗克曼决定低调进行调查。他在PSR网站(观察者网注:这个网站的主要用户是政治学研究生和助理教授,原意在提供工作信息,后来变为大杂烩论坛)上发布了拉科和格林研究报告中用到的一小部分数据,并指出数据存在两个不合理处:第一,参与调查者对同性婚姻以及同性恋者的态度在总体上持平,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这类有情感倾向的调查总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果,所以总要进行“二次测试”,以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第二,如果展开一项大规模调查,比如拉科研究里进行的这种,总会有人捣乱,给出的答案南辕北辙。但这组数据显示,参与调查者给出的回答,在口径上基本一致。“这种数据的平稳性显得不可思议。”
但这个帖子不久就被管理员删掉了。(直到拉科的造假丑闻被传得沸沸扬扬,这个帖子才得以重见天日。)布罗克曼感到有点挫败,他说,既然连这样的网站都不让发这个帖,那也许就不该再追究下去。
在此期间,布罗克曼仍然同拉科保持联络,他常向对方咨询研究方法,拉科给出的答案总是很含糊。当时布罗克曼正同卡拉一起进行一个项目,但他们发出去的13878份问卷只得到了100个人的回应——他们提供的钱并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布罗克曼又发邮件给拉科,但拉科没有给出明确回复。布罗克曼接着给拉科的一位合作者(他希望匿名)写信,对方给他转发了一份拉科写的邮件,在那封邮件下方,还附有拉科给杰森·彼得森的邮件。后者是uSamp的一位职员。
布罗克曼和卡拉决定联系这位杰森·彼得森,却发现uSamp根本没有这个人。他们又给这家公司发去邮件确认,得到的结果是:uSamp自始至终都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但直到这一阶段,两人仍然觉得火候未到。师友给出的建议仍然是:小心点,别暴露自己。
到5月16日,布罗克曼、卡拉,还有阿罗瑙(在发现彼得森并不存在后,他也加入了这个队伍)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卡拉在CCAP,一个知名的政治学大数据集里找到了疑似卡拉使用的原始数据。他们下载了那份数据,再对它们进行统计验定,得出的结果就是:拉科那份研究报告里用的数据,就来自CCAP。
第二天卡拉、布罗克曼和阿罗瑙就完成了他们的报告,并把它发给了格林。格林很快做了回复,说自己会要求《科学》杂志撤回拉科的文章。
之后格林告诉了拉科的导师,拉科承认说他并未像自己描述的那样去进行这些调查,但其余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格林在5月19日发出声明,要求撤回稿子,同日,布罗克曼三人发表了他们的报告。
5月20日,一个知名的科学博客《撤稿观察》将这个学术丑闻公之于众,由于访问人数过多,导致了网站的崩溃。
布罗克曼说,此事可以给后进的学人们一点启示,当你有所怀疑时,不要惧怕,只要以一种负责的学术态度去验证自己的观点,你的努力就不会白费。

链接:
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术造假之谜赛赞造假事件梗概
赛赞(Bengu Sezen)于2000年8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跟随导师萨麦斯教授(Dalibor Sames)从事碳氢键(C-H)选择性活化的研究。她先后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备受导师萨麦斯的喜爱,成为他的第一爱将。2005年,赛赞以一场精彩的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旋赴德国海德尔堡大学,后又在分子生物学专业获得了第二个博士学位。

赛赞(Bengu Sezen),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学生,通过学术造假,获得了博士学位。
但早在2002年,就有人对赛赞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提出质疑。接下来几年中,学界对赛赞研究结果的质疑声不断。2005年11月,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专门调查研讯委员会,并于次年2月宣布赛赞学术造假。随后,萨麦斯先后撤回了6篇与赛赞联合署名的关于碳氢键功能化的研究论文。
2006年8月到2007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对赛赞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起初她很合作,但在证据面前,她不仅狡辩,还采取各种方式回避调查,比如不回电邮、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甚至还搬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支持者的言论做挡箭牌,因为这些所谓支持者的IP地址是海德尔堡大学以及赛赞本人的电脑。接着她就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2011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撤销了赛赞的化学博士学位。
赛赞造假的铁证2010年11月,哥伦比亚大学经过了长达6—7个月的调查后,研究诚信办公室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分析直指赛赞研究行为不端的21个证据。研究诚信办公室在2010年11月29日的公报中称,赛赞在其博士论文以及3篇公开发表的论文里篡改、伪造、剽窃实验数据。
报告称,赛赞“至少在学位论文的第1、5、6章故意地编造和篡改核磁共振谱图。” “故意编造和篡改燃烧分析数据。”因为给赛赞做燃烧分析的公司从未向哥伦比亚大学收取过分析费用。赛赞后来解释说她找到了几家公司愿意免费为她进行分析,但是她提到的公司都公开反驳,并且声称和赛赞没有签过任何分析合同。
研究诚信办公室注意到,报告中最厚颜无耻的造假数据之一是“用4张31磷核磁共振谱图组成的合成图,其中某个峰已经用修正液或者另外一个相似的谱图掩盖。”据调查,其他的核磁共振谱图都是她从同事或者仪器默认的谱图中剽窃来的,因为这些图被保存在分析仪器的软件里。
诸多证据都表明赛赞的学位论文和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使用的实验数据都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并且不能充分证明实验的历程和结果。调查委员会在赛赞的实验记录本里也根本找不到任何实验数据同她已发表的数据相吻合。由此可知,赛赞在其学位论文和6篇以第一作者名义发表的论文中,大量的实验数据都是伪造的。
其实赛赞在一开始就使用骗术,而且更具戏剧性的是她造假的数据来源居然是本校的核磁共振分析仪。因为每个本校研究生要想使用核磁共振仪,必须先经过培训,并且一人一个账户和密码。但调查者了解到没有任何一个核磁共振分析是用赛赞的账户完成的。尽管赛赞曾告诉调查者她有一个自己的核磁共振账户和密码,但是这被证实又是一个谎言。
事实上,赛赞玩了一个骗人的游戏。她使用了其他萨麦斯实验室成员的账户名和密码,这些人在她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报告称,她造假的谱图中依稀可见其他实验室成员的账户名和文件名。但在赛赞实验记录本里找到的谱图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标记,而且这些谱图和她学位论文以及公开发表论文中的谱图数据相去甚远。当要求赛赞当面解释其中一张核磁共振谱图时,她称这张图是用400兆赫兹的仪器分析得到的。然而,这张谱图和另外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的谱图吻合,只是这张图标记的是用300兆赫兹的仪器分析得到的。事实是两个仪器根本不会得到完全相同的谱图。就此赛赞没有做解释。
至此事件告一段落,但是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谜团。比如:赛赞造假的动机是什么?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一所美国著名大学里一流的化学系,发生在赛赞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造假行为是怎样顺利进行而又为何一直没有被发现?
哥伦比亚大学并没有回应人们的迷惑,也拒绝对此事发表更多评论,除了精心准备的说辞外,绝口不提2000年至2005年间萨麦斯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段时间正是赛赞攻读博士学位,萨麦斯被聘为终身教授的5年。事发后,学校禁止萨麦斯或任何一个实验室人员公开谈论赛赞事件。
接到哥伦比亚大学造假调查报告和随附的研究诚信办公室分析报告之后,《化学与工程新闻》记者提交给大学一份关于该事件详细的问题清单,但学校再次拒绝回答。研究诚信办公室也拒绝进一步评论。
学界及社会热议
关注该事件的科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此事展开了热议。

赛赞的导师,萨麦斯教授(Dalibor Sames)因学生的学术造假行为,成为另一焦点人物。
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州立大学哲学副教授、科学伦理专家和博主——斯蒂姆维尔德评论说,“最使我惊愕的是项目负责人没有核实实验结果,也没有注意到对赛赞研究工作的诸多质疑。这是真正的伦理问题。”
美国大学协会联邦事务联合副出席沃尔尼茨也赞同地说:“相当难以置信。发生如此重大的造假事件,项目负责人是有责任的。我希望研究诚信办公室会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斯蒂姆维尔德教授还认为,在赛赞事件中校方更应该对学术界负责而出面澄清事实。如果校方能采取某种方式对赛赞事件进行公开对话是很有价值的,包括说明该事件为何没被发现以及今后如何避免类似的学术造假再次发生。“如果校方就此事件公开对话会更加让人感到安慰,尤其是当研究型大学的教学任务似乎已被卷进事件背景之时。正是校方的不回应让外界这样觉得。”
另有一些关注该事件的人认为,此事件暴漏了学术界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项目负责人有责任证实学生研究工作的真实性;当学术造假发生时,项目负责人应接受学校或基金机构的处理或处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学校应改变研究生仅依赖于一个教授的现实。
教授个人对研究生研究工作的指导和评价能决定他们科学生涯的轨迹,决定他们究竟能否在科学界有所作为。这起事件中至少有3名下属离开了萨麦斯实验室或者被解雇。他们每个人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尝试重现并延伸赛赞博士的研究工作。虽然不能确定他们离开的真实原因,但“浪费时间和精力,再加上不能重现研究工作的压力已经影响了这些学生正常的学习。”
博士造假的思考:路在何方赛赞可能再也不会从事科研工作,但能肯定,此事已给萨麦斯的伦理观和教学实践笼罩了一层阴影,甚至会影响到萨麦斯今后在本校以及其他知名研究型大学中的晋升和聘任。但萨麦斯今后的研究之路会怎样走谁也不知道。校方乃至学术界应该从此事件中吸取什么样教训也是值得学术界深思的问题。
《科学》论文造假被撤 ORI七年后对作者作出处罚
根据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网站2014年11月9日的一份声明,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R. Michael Roberts实验室以前的一位博士后,Kaushik Deb被查明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根据密苏里大学的调查和ORI的复查,发现Deb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科学》论文中存在“故意、肆无忌惮地捏造篡改数据”。
2006年末,在时任《科学》主编Donald Kennedy对改论文表示“关注”后,密苏里大学就开始进行调查。最终,该论文在2007年7月被撤销。
ORI如今已也终于调查完毕,发现Deb对篡改的图片应该负责。基于此,ORI禁止Deb在2017年11月17日前,禁止直接或间接承担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并不能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承担咨询角色。
一手交钱一手挂名:《科学美国人》调查论文贩卖造假问题
(VeraS/译)克劳斯·凯泽(Klaus Kayser)从事电子期刊的出版工作已经多年,他甚至记得当初给订户邮寄存有电子期刊的软盘。19年来的出版经验,让他对学术造假问题相当敏锐。他认为自己采用了不同寻常的方式以保护自己正在编辑出版的电子杂志《诊断病理学》(Diagnostic Pathology)。举例来说,为了避免作者冒名使用网络上的显微镜图片,他会要求作者发给他玻片原本。
尽管他的警觉性很高,但还是有些疑似不端的文章偷偷潜入了《诊断病理学》。比如,在2014年5月刊上,14篇文章中有6篇有着可疑的重复段落和其他不合常理之处。在《科学美国人》告诉他之前,凯泽显然并不知情,他对我们表示:“没人跟我说过这个,真是太感谢了。”
《诊断病理学》由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一般认为这是一本声誉良好的期刊,在主编凯泽的管理下,其期刊影响因子为2.411,这使得它在汤森路透的《期刊引文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稳居所有学术期刊排名的前25%,在76本病理期刊中位居第27名。期刊影响因子是根据文章被获得出版的学术文献所引用的次数来计算的,是衡量期刊声誉的粗糙标准。
凯泽的期刊并非特例。在过去几年中,在学术出版界的同行评议文献中,类似这样的违规信号时有出现,包括威立出版社(Wiley)、公共科学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泰勒弗朗西斯集团(Taylor & Francis),以及出版《科学美国人》的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这样的大型出版社,都有涉及。
在学术出版界(和研究界)快速变化的同时,明显的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对于将发表论文当作晋升升职的敲门砖,或是获得资金支持的研究者来说,谋得同行评议期刊上的一席之地的竞争相较以往已变得更加激烈。尽管互联网上的学术期刊数量激增,但供给仍旧赶不上数量庞大的学术产出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人们担忧,这种压力会滋生剽窃行为。
可疑的论文并不容易被辨识出来。单独来看,每篇研究论文似乎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在《科学美国人》的一项调查中,通过对100多篇学术文献的遣词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模板痕迹——这是一种信号,表明目前有一场大规模的对同行评议系统进行戏弄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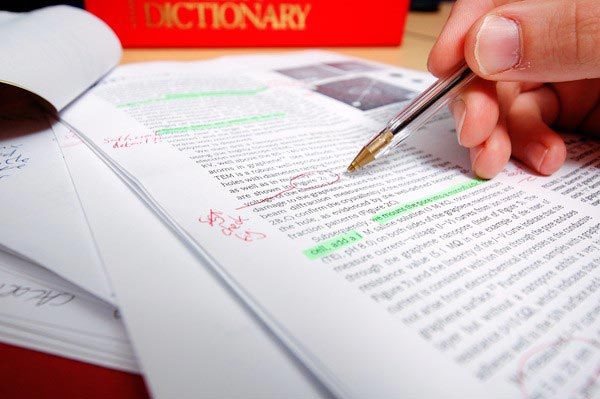
尽管本文涉及的很多期刊都有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但显然这种制度无法阻止论文造假问题的泛滥。图片来源:physicsworld.com
举例来说,发表在2014年《诊断病理学》5月刊上的一篇论文,表面上来看是一篇典型经过同行评议的荟萃分析论文,其作者为中国广西医科大学的8名研究者。在文中,作者评估了XPC基因的不同变种与胃癌之间是否有关联。他们发现这两者之间并无关联,并表示这不是该问题的最终定论: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large sample studies using standardized unbiased genotyping methods, homogeneous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nd well-matched controls. Moreover, gene–gene and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n the analysis. Such studies taking these factors into account may eventually lead to our bette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XPCpolymorphisms and gastric cancer risk.”
“然而,运用标准化的无偏的基因分型方法,对同类型胃癌病人和相应的治疗手段进行大样本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基因与基因、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应该在分析报告中有所考虑。综合这些因素的研究,可能最终会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XPC基因多态性与胃癌风险之间的关联。”
对于一篇极为普通的论文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结论,并不应当引发任何警报信号。但是,将其与《欧洲人类遗传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自然出版集团下属杂志)中,早些年发表的一篇关于CDH1基因的变种是否可能与前列腺癌(PCA)相关的荟萃分析论文进行对照的话: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large trials using standardized unbiased methods, homogeneous PCA patients and well-matched controls, with the assessors blinded to the data. Moreover, gene–gene and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n the analysis. Such studies taking these factors into account may eventually lead to our bette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DH1−160 C/A polymorphism and PCA risk.”
“然而,在评估者对数据单盲的情况下,运用标准化的无偏的基因分型方法,通过对同类型的前列腺癌病人和相应治疗手段进行大量实验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基因与基因、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应该在分析报告中有所考虑,综合这些因素的研究,可能最终会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CDH1-160C/A基因多态性与前列腺癌风险之间的关联。”
整段的措辞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包括“让我们更好更全面的理解”(lead to our bette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这个不怎么流畅的短语,唯一实质性的差别就是具体的基因(CDH1而不是XPC)和疾病(胃癌而不是前列腺癌)。
这并非一起简单的抄袭事件。很多看似独立的研究团队一直都在抄袭同一段文章——《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上的一篇论文中写的是可能最终会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XRCC1基因突变和甲状腺癌风险之间的关联;另一篇在《国际癌症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由威立出版社出版)上的论文则是可能最终会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XPA基因突变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联,诸如此类。有时候措辞之间的变化是很轻微的,但是在十几篇论文之中,我们都能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语句,只是嵌入了不同的基因和疾病名称——就像是“疯狂填词”游戏一般,游戏参与者们在一段文章中填入缺失的字眼。
我们还找到了其他像这样“填空研究”的样例。搜索短语“由于显然不相关而被排除在外”(excluded because of obvious irrelevance),我们找到了超过十几篇各式各样的研究论文。除了其中一篇外,其他均由中国研究者撰写;搜索“使用标准形式,公开发表的研究中的数据”(Using a standardized form, data from published studies),也找到了超过十几篇研究论文——依然,全部来自中国;搜索“贝格尔漏斗图”(Begger's funnel plot)则对应着几十篇文章——再一次,全部来自中国。
“贝格尔漏斗图”尤其能够说明问题,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贝格尔漏斗图这种东西。西班牙巴塞罗那基因调节中心的生物学家吉拉姆·菲利翁(Guillaume Filion)表示:“它不存在,这是关键。”一位名叫科林·贝格(Colin Begg)的统计学家和另一位名叫马提亚·埃格尔(Matthias Egger)的统计学家,各自发明了测试工具来寻找综合分析中的偏差——“贝格尔漏斗图”似乎只是这两个名字的意外杂交体。
“贝格尔”这一检测抄袭的方法是菲利翁偶然发现的。他在医学期刊文章中寻找行业动态时,发现这些论文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标题、类似的图表、以及相同的奇怪错误,就像“贝格尔漏斗图”。他猜测这些论文有同一个来源,尽管它们表面上是由不同的作者团队撰写的。“很难想像这28个人都是自己独立发明了一个统计测试的名字。”菲利翁说道,“所以我们非常震惊。”
通过在网上快速检索,我们可以发现有现成的成套服务提供,只需支付一定费用即可成为作者,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论文。研究者寻找在有声望的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捷径,而这些服务商们正是为了迎合这种需求。
今年(指2014年)11月的时候,《科学美国人》要求一位讲中文的记者与MedChina联系。MedChina是一家提供许多“论题出售”和学术期刊“文章所有权转让”服务的公司。记者假装想要购买学术论文的作者资格,与MedChina的代表商商谈。该代表解释说,这些论文已经基本算是被同行评议期刊接受,唯一需要做的只是一点编辑和润色工作,而价格则取决于目标刊物的影响因子,以及论文是实验性质的,还是荟萃分析性质的。在这次会谈中,MedChina的代表提供了一篇蛋白质与乳头状甲状腺癌的相关性进行荟萃分析的论文。这篇论文计划将要发表在一本期刊影响因子为3.353的期刊上,该论文的作者署名售价为人民币9.3万元。
MedChina出售的这篇论文最可能打算投稿的就是《临床内分泌学》(Clinical Endocrinology),这是5本影响因子为3.353的期刊之一,命题上也最吻合。这本期刊的高级编辑约翰·贝文(John Bevan)表示:“显然,这是一个极受关注的问题。想到这类事情一直在发生,并且越来越泛滥,我深感悲痛。”在《科学美国人》与他联系大约两周后,贝文确认了一篇可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乳头状甲状腺癌生物指标的,并且论文在修订过程中新加了一名作者。这篇论文最终被鉴定有问题,并被拒绝。
这些可疑的论文中,相当部分的资金支持来自中国政府。第一批被《科学美国人》辨识出来的100篇论文中,就有24篇收到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的资金支持;而另有17篇承认收到了其他政府来源的资金支持。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任杨卫确认,有24篇被《科学美国人》认定为可疑的论文,后来被交付到基金会的纪检监察审计局,该局每年调查几百起针对不当行为的指控。杨卫在邮件中写道:“每年NSFC都要执行几十起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但代笔行为则没有那么常见。”去年,该机构其中一起处罚案例涉及了一名从互联网上购买申请拨款提案的科学家。杨卫强调,NSFC正在采取措施对抗不端行为,包括近期安装的“相似检索”功能,以针对申款提案中可能发生的剽窃内容进行检索。(杨卫表示,该系统上线后的一年以来,已经从15万申款请求中检出了几百个“相当雷同”的内容)。但是一旦到了论文工厂层面,杨卫表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并无太多经验,十分乐意听取你们的建议。”
印迷 发表于 2015-6-7 14:19
大将军 发这样的帖子有失身份啊~~~~
中国13亿多国人,那些关注这个抄袭的人不会超过1千万人。而在这些关 ...
 加微信,拉你入群
加微信,拉你入群




 收藏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