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Princeton研究院贝特曼教授称华罗庚“作为一个科学的群众英雄的形象之于中国,有如爱因斯坦之于美国。”人们喜欢将成就不凡的人物予以神化,华罗庚也不例外,以至人们将他的刻苦勤奋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过分强调到超出其科学成果本身的程度。不过,对普通大众而言,科学家的精神感召力量胜之于学术启迪,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 点击图片看原图 |
前 言 1910年11月12日,这原本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有无数的人因为暴力、饥饿和灾难而离世,也有无数的生命在诞生。
这一天,在江苏金坛小城漕河岸边的一户小商人家中,诞生了一个名叫华罗庚的人。
他仅有金坛县中的初中学历,却成为世界级的天才数学家,他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出版后,爱因斯坦写信称:“你此一发现,为今后数学界开了一个重要源泉。”1950年新中国刚刚诞生,他毅然放弃在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理想的研究环境,回国支援国家建设。多年以后,他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同行这样评价他: “他原本可以为世界数学作出更大的贡献,但他选择了回国。如果没有他,中国的现代数学是不可想象的。”他是中国现代数学许多分支的主要开拓者,他在就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为新中国数学研究创立了许多必要的研究机构,他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数学家。为让数学直接作用于现实生活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用20年的时间奔波于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推广他的“统筹法”和“优选法”,“他给予自然界的东西远远地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他的东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受到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因此,“华罗庚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群众英雄的形象之于中国,如同爱因斯坦之于美国。”
因此,1910年11月12日,这个原本平常的日子也就显得非同寻常了。
 | 点击图片看原图 |
一、华罗庚与故乡金坛
假如可能,金坛人更愿意将他们居住的城市,更名为“华罗庚”,这一点,对那些长期出门在外的人来说,更加强烈。因为当金坛人走出金坛,走进更为广阔的世界,交流和沟通难免要介绍起自己的籍贯;人们对“金坛”二字的陌生和茫然是极为正常的事,就像许多金坛人对全国2000多个县中的绝大部分名字都闻所未闻一样。但一旦补充上一句“华罗庚的故乡”,对方便会立刻“哦!———”的一声,满脸振奋,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敬仰之情。
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金坛,1931年20岁那年到清华大学做助教后,仅有三次回金坛的经历,其间还有1925年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一年。华罗庚在金坛生活的时间,累计不过19年。但金坛的水养育了华罗庚,金坛的土地培植了华罗庚,金坛的人民和民俗文化,熏染了华罗庚,金坛人为此骄傲,并足以在走出金坛时作为一个“华罗庚的故乡人”而自豪。而实际上,华罗庚给予金坛人最多的还是他的奋斗精神、人格魅力和赤子情怀。在金坛,从冠以“华罗庚”之名的学校、公园,到浸染在金坛人骨子里的“开拓创新”精神,华罗庚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华罗庚精神对金坛人的激励,亦随处可见。
华罗庚也深深地挚爱过金坛这片土地,就像1950年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一样。每一次说到“金坛”这两个字,每一次遇到从金坛来的人,他都感到特别地亲,特别地动感情。
今年80岁的蔡志成先生一周前在家中向周刊记者回忆了他与华罗庚的交往。他儿时与年长10多岁的华罗庚有过短暂的交往,后来又曾任金坛县中(现华罗庚中学)校长和金坛县副县长,有机会参与了华罗庚三次回家乡的接待工作。蔡老先生回忆了1963年华罗庚第二次回金坛的一个小插曲:
那天他刚到金坛,是下午,很多金坛人还不知道。在县一招他的住处,他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蔡,我们上街去逛逛。”他知道,到明天再上街,就肯定会围上许多人,看不成他思念中的小街小巷了。
当时我不敢做主,就悄悄请示县里的上级领导,得到同意。我们俩就从原先一招所在地的司马坊开始走,到县府路、公园巷再到中山路、东门大街。我们俩都很高兴,但开始还没有人注意我们,华罗庚每遇到一个人都要主动搭讪,而且还是用金坛的本地话。在公园巷一户人家门口,他看到一个妇女在晾晒黄豆,就问她:
“咯(这)个黄豆是贰(你)自郭(己)种的啊?”
那个妇女没听懂。他就跟我说:
“咯(这)个宁(人)弗(不)是金坛宁(人)。”
我说,她是南下干部的家属,山东人,还听不懂金坛本地话呢!
1980年华罗庚第三次回金坛那一次,老蔡陪他到南新桥头华家老宅的旧址,那里因拓宽丹金漕河已没有了任何旧迹,华罗庚有些感伤。老蔡说:都是我的罪过啊!(当时他任副县长)。
华说:不是不是,金坛要发展的。
蔡老先生说,华罗庚的家乡观念特别重。家乡人送给他的金坛刻纸,他视若至宝,并赠送给外国同行;1950年代,清华的每一年新生入学,他都要主动去找金坛籍的学生,聊天合影。1980年代,华罗庚在收到家乡人寄给他的茅山绿茶后,情不自禁地在给蔡志成的信中写下了:
“香,香不过家乡茶,
亲,亲不过家乡人”
这句话,至今仍镌刻在华罗庚公园里他的铜像基座上。
像所有成就不凡的伟大人物一样,华罗庚少年、青年时代的经历,因其在世界数学界地位的奠定,曾经被赋予过种种传奇的色彩。
生活中的少年华罗庚,是平常而普通,不被人关注的;但青年华罗庚,却绝对是个“异类”,也正因为有了他的种种不同于常人的精神、毅力和行动,才造就了他随后的种种非凡的成就和业绩。
周刊记者在采写此稿过程中,有幸从汤钟音先生处获得大量鲜为人知的华罗庚的史料。退休前就职于金坛教育局的汤钟音1986年受命组建“金坛县华罗庚纪念活动办公室”,并直接参与了华罗庚纪念馆的修建和《卓越的人民数学家———华罗庚》一书的编写,并从此长期致力于对华罗庚的研究。期间他访问过许多华罗庚的亲属、同事、学生以及曾经与华罗庚有过接触的人物,使得我们在撰写此稿时有了一种特别的视角。
1925年,14岁的华罗庚在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却终因家境贫寒而被迫在一年后辍学回乡。1927年与本乡女子吴筱元完婚,这期间,他默默无闻。但18岁时,也即1929年秋天,他崭露头角,开始斗胆给上海的《科学》杂志投稿,《科学》在当时的中国是何等的刊物?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是李四光、竺可祯、翁文灏等名家。除此,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大学教授———苏步青。就是他在《科学》上的一篇文章,激起了华罗庚“弄斧到班门”的热情,并由此凿开了华罗庚曲步走进数学殿堂的大门。
1929年冬,突发伤寒的华罗庚几乎陷入了人生的绝境。半年后,死里逃生的他已是左腿残疾。1980年他在当时的金坛县中作《在困境中更要发愤求进》的讲学中回忆那段经历时,将其称作为人生的“第一劫”,他不迷信,但生死之劫给了他脱胎换骨般的精神改变。病愈后的1930年春天,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于上海的《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发表。华罗庚人生的起点由此拉开: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读到此文,连连惊叹,急问此人在何国留学?又问华氏是哪所大学的教授?待一并否定,且得知华罗庚乃金坛县中一小小教员时,立刻举荐其来清华。1933年,23岁的华罗庚,做了清华的两年旁听生后,被作为清华大学教授会破格接纳的一位正式助教,也是清华园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未经正统大学教育而获得教职的人。
青年华罗庚的刻苦和勤奋,已有无数的文章在传颂,但他在1966年对青年数学家沈有根的话依然让人感动:“一个自学的人的毅力,比上大学的在老师指导下学习的人的毅力,至少要大20倍才行。”
青年华罗庚也是幸运的,他天才般的智慧也得到了一批稀世伯乐的尝识和举荐,“他当时所在的金坛,其数学研究的条件与世界的距离,不下一百年,但他写的论文,在无法参考世界同行著作的前提下,达到了相等的水平,这是无法想象的奇迹。”美国数学家沙拉夫在他的《华罗庚传》中作出了如上的感叹。华罗庚最得意的门生,也是因撰写《华罗庚传》而一度引起学界热烈讨论并提出“科学家传记应是科学家才有资格来写”的观点的王元先生,在2000年参加金坛华罗庚诞辰90 周年纪念活动时,曾说,华老在《科学》上发表论文,然后被清华熊庆来看中,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在这前面,假如没有金坛县中的学者校长韩大受和学养丰厚的留法生、《神曲》的中译者王维克的浇灌和提携,那一切,都是很难成为可能的。
 | 点击图片看原图 |
图:陈省身 我与华罗庚
“机会总是青睐于那些勤奋并随时准备着的人。”清华助教华罗庚有整整三年未发一篇论文,而一旦发表,又不可收拾,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1936-1938年,他赴英留学剑桥的两年间,他在数论上的研究,产生了令世界惊叹的成果。据王元在《我的老师华罗庚》中说,很多数论重要问题的解决,都可归结为某种三角和的估计,三角和的估计是近代数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高斯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关于二次多项式对应的完整三角和就称为高斯和。但高斯本人只解决了它的最佳估计问题,而华罗庚却在他200多年后(即1938年)解决了任意多项式、多数为整数的一般完整三角和的最佳估计。国际上为此称华罗庚关于完整三角和的成果为“华氏定理”。
1938年,27岁的华罗庚回国成了西南联大的年轻教授。
1945年前后,随着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诞生和俄、日、德、匈、英文版的出版,34岁的华罗庚已经在国际数学界声名鹤起,他的数学理论成果成为国际上一些大数学家们,“在研究中所必需征引的文献。”(《华罗庚传》)
青年华罗庚,在国际数学界已经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位,而像他这样通过由自学攀上世界高峰的数学家,世界历史上仅有两位(另一位是前苏联的)。
三、假如当年华罗庚不回祖国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回望历史,人们却无法不因某个个人力量的巨大及其产生影响的深远而作种种可能的想象。
中国古代数学曾经有过极为光荣的传统和贡献,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所以渐渐地落后了。而现代数学研究是从20世纪的20年代开始的。
华罗庚这个从金坛乡间走进数学殿堂的稀世奇才,起点却是国际水准的,从最初驳苏家驹的论文在《科学》上一鸣惊人,到远赴剑桥求学。在剑桥,他谢绝了数学系主任哈定“两年可得博士学位”的推荐(正常情况下要7年时间),但他却“出色地解决了一个个当时著名的难题,如华林问题、泰利问题等。他的论文篇篇都是超水平的,专攻分析者或专攻数论者都不了解。30年代看得懂华先生论文的人,据说只有苏联的科学院院长一个,另外法国两人,美国有一人,印度有一人”(新竹:《清华校友通讯》第86期)
当《堆垒素数论》外文版出版时,爱因斯坦从普林斯顿研究室给中央研究院发来专函:“你此一发现,为今后数学界开了一个重要源泉”(《清华校友通讯》复12期)。“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二十世纪数论的所有至高观点,他的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美国数学家狄锐克·莱麦尔)。1977年,由美国数学家沙拉夫撰写的《华罗庚传》中,第一句话就称华罗庚为“多方面名列世界前茅的数学家”。“他的《堆垒素数论》、《数论引论》、《典型域上的调合分析》以及与万哲先合作的《典型群》等数学著作无一不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震动”。
1946年9月,华罗庚作为Princeton高等研究所的高等研究员、Illinois大学的终身教授。凭借着世界上已有的几乎是最优厚的研究条件、最完备的资料库,在最顶尖的数学领域驰骋。除此,还有相比于国内十分优厚的生活待遇以及研究者赖以支撑的高端群体。
但这一切,仅仅维持到1949年年底,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一心想报效祖国的华罗庚激情澎湃,他毅然发表了一份震撼了无数海外学子,也激励了万千中华儿女的《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并毅然决定,立即投身于祖国,他的同事、美国Princeton高等研究院著名数学家艾特尔·赛尔伯格教授在多年之后评价说:“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数学也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回国,中国数学会怎么样。”
回到祖国,百废待兴,但华罗庚充满了无限的热忱和激情,他要把世界上最高端、最优秀的数学研究成果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迫切地希望远远地落后于世界数学界的中国,能够迅速成长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数学家。
他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实际上,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愈来愈放到第二位上考虑了。
1953年,身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组织成立了数论组,后来又成立了代数研究组,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王元、陈景润等一批青年数学家在他的直接培养下,迅速成长。“他还热情支持成立拓朴学、微分方程、概率统计、泛函分析和数理逻辑等研究。特别在建所初期,就很重视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工作……他支持了他的老师熊庆来先生回国工作,使熊老晚年还能为中国数学作贡献,培养了杨乐、张广厚等学生。吴文俊是华老邀请来数学所主持几何学、拓朴学研究的……其他如关肇直、王光寅、丁石兹、钟家庆等20多位年轻数学家,都无一不在华老的悉心指导下获得成果的”(王元:《我的老师华罗庚》)。
1946年,华罗庚访苏曾发现,许多搞实用科学的人最后常常会转入数学中来,因为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从数学中才能得到解答。他曾说“头脑受过数学训练的人,是不用担心他们的出路的,而漠视数学的民族,肯定是不能进步的民族。”
 | 点击图片看原图 |
华罗庚对中国数学事业的贡献,中国人自己尚未来得及细细盘点,而国际数学界已清晰地感受到他以卓越的成就成为“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个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 (1985年8月25日《光明日报》)他回国后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之职,不仅在研究机构的设置、制度的建立和方向的确立上,与国际接轨,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之先河,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数学精英。1980年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数学家科拉达的《华罗庚形成了中国的数学》的文章,称:“华罗庚培养、影响与教育了中国的好几代数学家,我相信这些人对中国数学的发展是会长久地起作用的。”
1981年,美国《旧金山周报》在访问华罗庚时曾问道:
“你回国了,不后悔吗?”
因为很显然,回国后,华罗庚个人的数学研究已没有了人们期望中的那样成果卓著。
华罗庚用当年决定回国时的想法作了回答:
“我留下是很容易的,在美国对我的妻子、儿女及我的工作都是重要的,我回去与否呢?最后我决定了,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是穷人出身,革命有利于穷人。而且我想我可以做一些对中国数学来说,是重要的事情……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让数学这样落后呢?我们应该赶上去,我想我们是能够赶上去的。”
他尽心尽力地做了,他也做到了。中国早期著名的新闻记者赵浩生在对华罗庚访问后写道:“华罗庚确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光荣的名家,因为有这个名字,我们的国家才没有在国际理论科学界中被人遗忘;因为有这个名字,在一片荒芜的中国理论科学界中,才存在着一点可足欣慰的希望。”中国数学的形成还有其他重要人物和因素,但华罗庚的贡献和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四、晚年华罗庚
从1965年开始,华罗庚的工作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工作的重点从基础的理论数学研究转移到了普及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的数学方法上。他选择了以改进工艺为主的“优选法”和改善组织管理的“统筹法”来普及。为了让普通工人能明白,他对这两个方法作了简化,以最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他写的两本小册子几乎都避免了数学语言。特别是他身体力行,不顾劳累和年老多病的身体,在近20年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到过无数的工厂,为群众讲授数学,解决实际问题。20多年中,他从未动摇过为国民经济建设从事数学普及工作的决心。
 | 点击图片看原图 |
对此,许多人深表惋惜,也有人怀有种种的猜测。
华罗庚最亲近的学生王元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仿佛是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他的看法。
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专著出版后,不顾已经成为著名数论学家的荣誉,毅然放弃了数论研究,宁肯另起炉灶。从四十年代开始,他进入了代数领域工作。解析数论与代数是两个不同风格的数学领域,一个是精密分析,一个则要求漂亮简洁。但华罗庚对王元说:“我如果继续搞三角和,大概顶多再写几篇好文章,也就结束了。”而这样的转折,却使他在解论、典型群、矩阵几何等方面又取得了卓越成就,并开辟了自守函数与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把分析与代数的技巧高度结合起来。(王元:《华罗庚传》)
如果说,四十年代的这种研究方面的转移是更多地从个人事业角度考虑的结果的话,那么,60年代中期走出“象牙塔”开始的“双法”推广,则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他又一次站在高山之巅,任山风拂动灰白须发,眼噙泪珠,向死难者致哀。———两位解放军士兵为排破哑炮故障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1965年,祖国西南大三线工地。”(1985年8月28日《光明日报》:《他从高山走向大地》)
血的震撼,在数学家的心海激起层层波澜:为什么不能在生产过程中,使之工艺参数、原料配比等处于最佳状态,从而生产出高质量的雷管?为什么工厂生产的雷管,非得等到现场使用之后,才能判断它们是否合格?为什么不能事先检出次品?为什么不采用科学的方法合理抽样?他认识到:新中国许多工农业生产建设中,生产工艺落后,生产水平不高,但生产潜力很大,一旦把新科学新技术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就能转化为很大的生产力,对国家作出大的贡献。他决心走一条中国式的推广应用数学的道路。
大三线工程大多摆列于崇山峻岭之中,曲折蛇行的临时公路傍峭壁、临深渊,行车如过鬼门关,但他毫不畏惧。他年岁渐高,血压渐高,除足疾,又患心脏病,医生嘱咐每日工作不能超过两小时,但他工作起来总是争分夺秒,忘了医嘱。在两个矿区,他常常戴着氧气袋坚持工作,他 “夏战浙豫冒酷暑,冬战松辽斗寒冰,”结果惹得老伴也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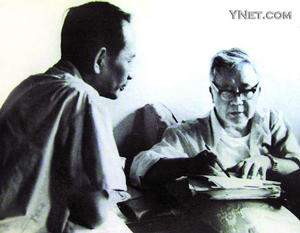 | 点击图片看原图 |
他的“华氏双法”在国计民生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谓无所不包,无以计算,大到企业重大经营决策、矿山开采、粮食增产、油脂提炼等等,小到七个开关如何管住一个灯。近20年间,他的足迹遍布除西藏、青海、宁夏三处医生不准去的地方之外的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10多个省成立了“双法”研究会,数万人投入了这一工作。有学者曾对晚年华罗庚放弃理论数学研究转入应用数学的推广这一巨大转变作过种种推测,认为是华迫于现实政治的无奈选择。但笔者细细研究,则认为是华罗庚思想发展过程中,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自然演变。
一、数学理论只有和应用配合,才有益。这一主张早在1946年华罗庚访苏时就已产生,他在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参观(莫斯科大学)之后,我想到我们中国科学界的情形……中国科学要想进步,除去必须注意到理论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注意到理论与应用的配合;理论如果不和应用配合,则两相脱节,而欲科学发达,实在是不可能。”(1947年夏秋版:《时与文》杂志),而回国后的华罗庚,深陷于一种数学理论无用论的错误观念中,与其说他是要起而反驳,倒不如说是实践他内心积压已久的理想:“其实,数学并不是无用武之地,而是因为没有中间的这一道桥梁,把数学和应用连接起来。”(出处同上)
二、有人认为推广“双法”是华对现实政治的迎合。但华罗庚在接受知名记者赵浩生采访时曾坦言,科学与政治实在无法分开,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者,一定要努力设法使政治与科学分开,作如此挣扎,不能够有细微的成就,这是中国科学研究者最大的苦闷。尽管有学者认为华在晚年放弃理论数学研究,从事实用数学推广是一种损失,但不可否认,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推广“双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空头政治,使许多部门回到了重技术、抓生产的道路上,而且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世界级数学大师在国际上的独特地位。他曾说过:“假如有一天,我的梦想实现了,中国真正开始和平建设,我想科学决不是太次要的问题,我们决不能等待到真正需要科学的时候再开始研究科学。”
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予以充分的肯定和大力的支持。胡耀邦在致华罗庚的信中说:“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
国际数学泰斗劳埃尔·熊飞尔德曾说:“华罗庚教授研究和著作范围之广,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受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
美国学者贝特曼教授认为:“现在还没有一个西方的数学家及得上他被拥戴的水平。”而且他认为华罗庚在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科学的群众英雄的形象,有如爱因斯坦之在美国。
1979年,68岁的华罗庚被法国南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除此之外,他还享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的荣誉。但在许多场合,他都毫不忌讳地自称为“金坛县中的一个初中毕业生”。他为人类贡献了200余篇论文,10部专著,创造了一批新的数学理论和学术概念。1985年6月12日,他倒在了日本东京大学的学术讲座上,实践了他自己“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诺言。
相关链接
毫无疑问,华罗庚不仅是金坛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而实际上,“华罗庚”这三个字所显现出的效应,已不仅仅局限于数学界。
华罗庚逝世后,1986年,他的母校金坛县中便改名为华罗庚中学,至今该校仍保持着高一新生入学参观校史、学习华罗庚精神的传统;他的家乡金坛还建造了一座华罗庚纪念馆,并将城市里惟一的公园改名为华罗庚公园;金坛撤县改市之后,又开发了华罗庚科技城(金坛经济开发区的前身),举办“华交会”,从而迈开了向工业城市发展的步伐;2003年,一所“华罗庚实验学校”又在金坛成立。甚至,在北京也曾有一座学校叫华罗庚学校,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超常教育实验基地,专门探索鉴别、选拔、培养超常儿童的方法,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教育之路。
1986年,团中央、中央电视台青少年节目中心、中国数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了全国“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以引导少年儿童学习华罗庚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献身科学的崇高品质。此项赛事原本只邀请地级市的学校选手参加,但因为金坛是华罗庚的故乡,被破格允许参加。并且,金坛还作为东道主,举办了第五届“华杯赛”。
1992年,中国数学会又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共同设立了“华罗庚数学奖”,主要奖励有杰出贡献的中国数学家。目前,“华罗庚数学奖”和“陈省身数学奖”是中国数学界级别最高、分量最重的两个奖项。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我国曾经出现过一股“华罗庚热”,涌现出不少关于华罗庚的文艺作品。如顾迈南的《华罗庚传》、孔章圣的《华罗庚研究》、石楠和江村的《数圣华罗庚》、王元的《华罗庚传》等一批研究华罗庚的书籍相继出版。
早在1980年代初,就有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华罗庚》,还被评为第二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优秀连续剧”;1997年,浙江电视台也投拍一部同名的电视剧;2000年,曾经播出过一部轰动一时的连续剧《我亲爱的祖国》,该剧以钱学森、华罗庚等人为原型,反映了那一代海外学子历经磨难、不忘报国的赤子之心;同年,金坛锡剧团的《少年华罗庚》一剧,又先后获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奖和文化部第十届“文华奖”新剧目奖。
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40年代末,华罗庚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结识了“电脑之父”冯·诺依曼,并参观了他的实验室。从那时起,华罗庚便在心中勾勒中国电脑的雏形。
1953年,华罗庚受命在中科院数学所内,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1956年,他又被任命为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负责起草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规划实施的结果,促成了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诞生,也为1958年,我国第一台国产计算机103机的发明,作了充分的条件准备。
1984年,华罗庚当年的助手殷步九创立了著名的四通公司,曾经风云一时的四通排版软件就是该公司的产品。此后,殷步九又成立了“华罗庚软件研究所”,专门从事《世纪桥》项目有关的“直接法”与“事务逻辑”技术的深入研究工作。同时他利用华罗庚的“直接法”和“系统优化”理论,建立政府级和企业级的电子政务和企业资源优化系统等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和系统优化模型。为进一步推广成果,殷步九还在广东汕头建立了中国模式的新型软件工厂———华罗庚软件基地。
事实上,我国的项目管理历史就起源于华罗庚1965年开始的“双推”工作。到1980年代后期,我国已经开发出了基于统筹法和网络技术的项目管理软件,“北京统筹法与管理科学研究会”首先在全国的建筑领域大力推广,使各地建筑业的项目管理水平大大提高。
为了推动我国的项目管理研究与应用,1992年华罗庚生前创建的“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成立了“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对推动我国项目管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3年,非典结束之后,中科院有关部门,结合统筹法理论,在网络计划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博弈网络技术”,这项研究不仅在项目管理的理论上提出了新方向,而且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也很有意义。因此,有媒体称这是“华罗庚的统筹法被赋以新的内涵”。

 加微信,拉你入群
加微信,拉你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