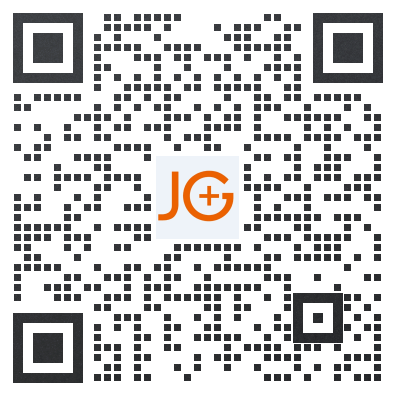最近,随着台湾各民间党领袖的来访,京城三大名校的校长被推上了前台。但不巧,清华校长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了“洋相”,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书法体例里翻了船!于是,各方热炒,觉得给中国人丢了脸。对国人而言,“丢面子”的是本便不小,更何况还事关“国仪”,当然是决不能允许的。所以,人们便自觉地把目光移到了下一位登台亮相的人大校长——纪宝成先生身上。
还好,行政出身的纪校长举止得当,并没让人觉得有何不妥。但是,对一些人而言,鸡蛋里总是能挑出骨头的。举止没错,言谈便成了“寻骨头”的所在。如此,“七月流火”便成了某些人眼里的“笑柄”。对一些人而言,更为可笑的还在于,纪校长是人大“国学院”的始作俑者:身为“国学院领袖”,岂能用错国学“典故”?
然而,纪校长的“七月流火”真的用错了么?如此“寻骨头”的思维又说明了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所谓“国学”是足以“吓坏”一批人的,“博大精深”不说,而且“汗牛充栋”。不仅如此,国学经典多以古文、繁体字作为载体,现代人想从“源头”去了解“真意”,的确是非常难的。通过上个世纪初“胡适们”的努力,白话文逐渐畅行,虽被攻击为“割断”历史,但博古通今的“白话先生”们还是通过自己的“翻译”,让许多晦涩难懂的古文变得通俗易懂。自此,山野村夫便有了在“形而上”方面的发言权,而识文断字从此也不再单单是秀才们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在当今社会不仅已经部分地演化成了白话文,而且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也可避免地要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而当这种新的含义被社会逐渐接受之后,它便有了其新的约定俗成的含义。这就像过去人们习惯于旧历计时,如今大众更习惯于数着新历过日子一样。而这其中,我以为便包括这个所谓《诗经》中“七月流火”!
试问,当今社会里,除了极少部分专业人士和古籍爱好者,到底有多少人会去研究《诗经》呢?如果没多少人去“研究”,那么谁又能字面上想到“七月流火”的本意?事实上,现代人虽然继承了“七月流火”的说法,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阳历7月的立场来理解“流火”,而绝不会去想到“七月便是如今的9月”等等艰涩的经典内涵。是啊,现代中国人的七月的确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日子,言其“流火”又有何不可呢?
为了佐证“七月流火”已被“约定俗成”,我在这里讲一个中国股市许多投资者都知道的例子。大致是在2003年6月末吧,一个股评家在电视里预言“中国股市在7月将有不小的行情”,为了表述得形象些,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七月流金”。但后来,“七月流金”没成,到因为股市在7月的继续下跌,成了让股民痛苦的“七月流血”!在此,该股评家显然是把“七月流火”“演绎”成了“七月流金”,但7000万投资者并没人笑话该股评家引用“七月流火”有违《诗经》本意,笑得倒是他老人家的预测与实际走势的反差!
在此,笔者并无贬低该股评家的意思,因为事实上,预测行情本便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四年来中国股市的拙劣走势已经让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沦为“笑料”!
我想借此说明的是,在当今中国,“七月流火”早已超越了《诗经》的本意,也早已超越了那些“国学典故”爱好者们的狭隘视野。在比如古人的另一句“名言”“桃之夭夭”吧,她本是形容桃花盛开婀娜多姿的美态,但后来呢,却被历史演绎成了“逃之夭夭”,其含义完全是“风牛马”的事情了。
可以看到,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同一词汇的语义语境也在发生在巨大的变化。如今,当网络语言都能大行其道而让“网外人”一头雾水的今天,守残抱缺,拿出《诗经》来说事“搞笑”,最终便不免成为别人的笑话!人大的纪校长倡导研究国学,当然理当在国学上也有所用心,但单凭“七月流火”却并不能断言纪校长研究不够,“准备不足”!毕竟,“七月流火”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新意;毕竟,这是在欢迎台湾新党主席,而并非是在举办“国学研讨会”;毕竟,人大的学院很多,纪宝成校长管理的也并非只有一个“国学院”!
当然,提出“七月流火”的“挑骨头”尝试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
首先,它让众多忙于经济的国人想起了《诗经》,知道了“七月流火”的本意,也算是一种知识普及。因为据网络调查调查,此前有将近80%的国人并不知道或者并不完全了解“七月流火”的本来含义;
其次,它让“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变得更加家喻户晓,让人大新成立的国学院变得更加“知名”,无形中为其作了一次免费广告。纪校长的“笑话”纯属一些文人学者们的“挑骨头”思维所致,所以对人大以及纪校长的声誉并无多大杀伤力。
第三,它让纪校长一样总在“前台”的权威们明白了一件事,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随着媒体监督力度和竞争力度的增强,随着网络媒体和博客时代的来临,所谓“权威”也便越来越容易受到“大众”和传媒的挑战,其在“台面”上乃至镁光灯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普罗大众眼里茶余饭后的“文化美餐”。
以前,“权威”或许只属于行政圈或者学术界,今后,“权威”还将属于参与意识不断强化的公众,至少,公众的评判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权威”的市场价值。
市场化改革在颠覆传统价值,在挑战传统权威,也在于其与传统、计划的碰撞中不断“高效”地制造着各种“搞笑”新闻。
这是一条躁动的暗流,它不时地在激荡中“冒泡”,让人流完“鼻血”再“流火”!只不过,有的只是昙花一现、纸醉金迷的“娱乐盛宴”,有的却是地地道道的“思想大餐”!
然而,“七月流火”算什么呢?哪个都算不上!我以为,这则新闻有些无聊,很像鲁迅笔下《孔已己〉里茴香豆的“回有四种写法”的高明。道理很简单,在某些不务“国学”精髓却只会在字面上做文章的“权威”眼里,“七月流火”或许是个笑料,但在我看来,它毕竟和“吹毛求屁(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吹毛求屁”!懂么?或许,这才是“七月流火”问题的“中心区(枢)纽”吧。
(吹毛求屁 是笔者在“七月流火”新闻回贴中看到的,堪称妙喻,而笔者曾在一个工厂的团委会上亲耳听到有人把“中心枢纽”一本正经地读为“中心区纽!)
7月12日,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欢迎台湾新党主席的致辞中,错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热的意思。一时间网上充斥了对其冷嘲热讽。但是也有一些人为其辩护,“语言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约定俗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词语的意义本来就可以随时代变迁而变迁。”“在当今中国,‘七月流火’早已超越了《诗经》的本意,也早已超越了那些‘国学典故’爱好者们的狭隘视野。”云云。
与不久前纪校长生造出“脊续”一词,人大中文系的教授跳出来为其保驾,不同的是,这些辩护并非全无道理。“七月流火”一词在现在文章中的确经常被用于表示七月份很炎热,海峡两岸都是如此。而一个成语如果经常被错用的确也能被接受成正解,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每况愈下”、“出尔反尔”、“兴高采烈”、“空穴来风”等等常见成语在现在的用法都已脱离原意,甚至恰好与原意相反。
上面这些例子已经约定俗成,被收进了辞典,原意反而没有人用了,而“七月流火” 并不属于此类。一方面许多人在误用这个成语,一方面专家们一直不认同这种用法,反复纠正:“七月流火”指的是夏历七月黄昏时大火星从西方落下去,表示天气转凉进入秋天了……说不定哪天专家们纠正得烦了,也将错就错承认老百姓们的创造。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仍然必须认定纪校长的确用错了成语。
一般人不懂得“七月流火”的晦涩正解,用错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纪校长并不是一般人,老百姓可以错,他却错不得,因为他不仅是“国学典故”爱好者,而且最近正在大力提倡国学,人民大学为此还成立了国学院。这个小插曲的可笑之处正在于它表明了这位国学的大力提倡者其实是连《诗经》最著名的篇章之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都没有读过的,其提倡国学纯属附庸风雅、叶公好龙。这就像当年鲁迅反复嘲笑章士钊错把“每下愈况”写成“每况愈下”,虽然现在错误的“每况愈下”几乎已淘汰了正确的“每下愈况”,但是也无法挽回当时章士钊提倡文言而自己不通文言的尴尬。
经过这场风波之后,会有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七月流火”的真正含义,减少对它的误用。也许“七月流火”竟会因此而终止了以讹传讹、约定俗成的演变。果真如此的话,倒也算得上人大校长以自己的声誉为代价为国学做出了一个独特的贡献。如果要正儿八经地提倡国学,还是请先闭门修练提高自己的国学修养之后再说吧,否则岂不是在误人子弟?
SOHU们,从开始就不怀好意?请让我们高举《细节决定成败》的伟大旗帜,把搜狐们,当然更包括那些日益把低俗和媚俗当做信条的媒体们,在这场新党人大一行中的狗崽表演翻出来给大家看。7月12日,郁慕民人大演讲。新浪视频直播,都至于首页和新闻中心的头条,新闻专题也做了全面的跟踪报道。搜狐没有视频直播,虽然看了文字直播的网友有多么不满,另外在新闻重要性处理上也没有跟新浪一样,放置在首页和新闻中心的头条。但这似乎无关紧要,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理念。当绝大多数人还沉浸在郁慕民先生慷慨激昂的脱稿演讲、鲜明的人格魅力和政策主张以及人大很好的主场表现的时候——7月15日,搜狐首页和新闻中心国内头条固定,并很快被制造为专题的一则新闻把我们拉倒一场口水大战中——人大校长曾经大力提倡国学 迎接新党时用错典故!同期还还推出多少人知道“七月流火”的含义专项调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调查中65.75%以上的人以前不知道这个典故的含义被莫名其妙地错误地处理成65.75%以上的人知道。请宽恕,学中文的就是喜欢寻章摘句玩推敲,我想它应该表述为你先前是否知道七月流火的“典故含义”更为妥帖。不过这个问题就留给语言学家们去解决!我们还是来揣摩搜狐狗崽们在处理这些新闻时的动机和心理。当我们找到该文的源头《中国青年报》的主页,我们发现中青报的原文原标题是《从纪校长的“七月流火”说起》,中青报并没有当新闻处理,而是处理成评论,位置在青年评论版。这算什么?是想让们感谢搜狐带领全国人民参与到一场学习细节的全民运动,参与到一场对国学的批判和对一个校长群呕的狂欢中来吗??我看,这是一场从开始就不怀好意的对新闻精神和新闻中的主角的亵渎和不敬,而事情的发端则可以拉回到人大四五月间高调的成立国学院,准备举起复兴国学的旗子,于是各色人等变跳出来了,他们大概是找到了一个跳出来的理由。7月19日,上升到对纪校长人格的侮辱!1 9日,搜狐再次行动。这一次是转载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但同样搜狐把它处理为新闻,并放在首页和新闻中心国内新闻版的显著位置,醒目的标题跟人咬狗的一样具有轰动效果——人大校长又出丑了!潜台词好像是纪校长曾经出过丑,今天“再接再厉”。我想光这一点老纪就可以把你推上法庭,提醒处理这条新闻的责编或主编,这已经超出新闻本身而上升对他人人格的主观侮辱了,这些行为实在是对整个新闻界的亵渎。与你们不同,现在老纪以及整个人大选择的是——沉默和宽容的君子之道。但这并不影响和妨碍我们这些人大门下的走狗可以对你做出反击的权利——我并不会为暂时做“走狗”而自卑,中国人的历史很多程度上就是一部从争取做走狗到坐稳了走狗再到争取做主子的历史,大家都好不了多少,五十步笑百步就免了。至少你丫新闻用词不严谨、新闻报道处理不严肃、严重掺入主观色彩的小样,就着实令偶们像冯导那样愤怒——你丫找抽啊?!当然,我是不会动手的。我惊诧的是,你们把红卫兵扣帽子的精神发扬的这么好,而且还弄得全国都一地鸡毛,实在佩服。媒体主观意志的泛滥,真正的新闻主题被边缘化了 各位看官,大家看到这里会发现,在这场个别媒体掀起,搜狐们推波助澜的近乎妖魔化的声浪当中,事件的原本主题——新党精彩的表演,人大的精彩表演,新党独立而艰难的生存景况,新党旗帜鲜明的反台独、民族统一主张,郁慕民独特的人格魅力,人大学生的发挥、人大赠送礼品的经典,以及新党党员雷倩在演讲后接受央视采访所发出的,也许我们是台湾最后一代敢大声说自己是中国人的悲歌,都一一被边缘化了,大家都忙着去咬纪校长的小辫去了,就像新党郁慕民还不如台湾女星林志玲大连坠马热的自我解嘲,这年头,中国人民不缺思想,就缺娱乐!清华李希光老师成名作《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所中揭示的媒体妖魔化的社会功能,在中国本土也制造了一个光辉而生动的案例,不知道可不可以编入下一部新闻史?当媒体在事件中注入更多的主观,当媒体自甘堕落去舍本逐末,当媒体企图在事件中让自己也成为主角,这绝对不是一件好消息。有好事者完全可以上升到媒体的独立人格、媒体自由的限度、媒体对司法行政等公共管理的干预与越位等一大堆宏大的命题上来,展开几场浩浩荡荡的论战。做新闻做得这么猥琐,以及反国学者们的标志性国学行径,发人深思!到此,我个人深深觉得做新闻做到这种程度,真他妈的猥琐!比港台娱乐媒体的狗崽队还三八,整个像被压制或强暴过后,甫一挣脱牢笼变怀着一颗睚眦必报的心,拣起石头就朝压迫者扔将过去。而且非常不幸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统国学中的文人相轻、睚眦必报、做人不厚道等一连串垃圾,却被某些反抗辨证地复兴国学的人们完好地继承着,并时刻发扬光大着。我总是善良的想,也许是他们自己的自省和自觉吧,他们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传统劣根性,所以要群起攻击任何试图复兴国学的冲动,他们大概是要亲自把自己做为案例,提醒纪校长和人大要“脊续”国学,首先得革了他们的命,革了余毒和垃圾的命,新国学才有希望。果如此,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记得以前有一次跟搜狐内容副总裁方刚交流,他曾经有些郁闷的说,搜狐的新闻已经做过新浪啦,但是却抗拒不了新浪新闻还是网民第一选择的宿命,为此一直很迷茫。我越来越理解这种迷茫,而且现在看来,这种迷茫还会继续下去。我无意抬高新浪,我只不过是在学习并发扬搜狐们的这些狗崽们管中窥豹、追求细节的精髓,以小看大。于是自己突然变得很茫然,很神伤。因为从这起搜狐们、狗崽们抓住纪校长的辫子不放的现代文字狱中,我越发感觉到国学中那些吃人的东西还在释放,以及还在吃人和害人的悲凉。这些传统的遗毒和垃圾不除,国学精华的辨证继承和发扬就只会停留为一种梦想。 此外,我还为一个我知道人家,人家不知道我的张朝阳神伤,这个40多岁但仍然不停地忙着走秀的王老五,是不是该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搜狐等网媒要想跻身真正的主流传媒阵营,要想扮演更具建设性角色,是不是要多一点严肃,多一点厚道,多一点责任感,多一点道德?一群缺乏使命感、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人是注定不会成为主流的,即使偶尔作奸犯科做上了主子,也会很快被人掀翻马下的。也不知道这句明言到底是谁说的了,暂且先算在我自己的头上吧。或许搜狐们根本并不在乎什么主流不主流,只要能勾引到网民的眼球既而他们的钱包就足够了,那就当我对狐弹琴吧。抱歉,我又用错典故了,应该对牛弹琴才对!还有那份越来越沦陷的中国青年报,我已经不看它好多年!
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时,偶也将把自己过剩的精力拉回到自己喜欢的电信观察上来!感谢各位的阅读和捧场!
从人大校长犯错说起(金仕并) |
作者: 刘夙 | 2005年07月22日11时42分 | |
7月12日,台湾新党访问人民大学,在新党主席郁慕明的演讲之前,人大校长纪宝成在致辞的第一句就犯了低级错误,竟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热的意思。清华大学的顾秉林校长这回不寂寞了:以后人们可以顾、纪并提,共同作为中国教育的笑话,顾秉林也总算比先前只有一个国关的刘江永教授陪衬更显得体面些。 这事在网上讨论起来之后,颇有一些人替纪宝成开脱,什么“这正说明国学复兴很迫切”呀,“词语的意义本来就可以随时代变迁而变迁”呀,那理由是五花八门的。最搞笑的是天涯时空上的一个叫徐志频的人,写了篇长长的《古诗岂能沦为专吃中国一流大学校长的工具?》(转载见http://www.pkucn.com/redirect.php?tid=149067&goto=lastpost)。里面先装模作样地说“我们必须承认,纪宝成这错误犯得确实也够低级”,接着却说“至少我念初中那阵就知道了‘七月流火’这火是指火星”。作者大概是想顺便显示一下自己受的中学教育比纪宝成强,结果却是更狠地搧了自己一个耳光。“七月流火”的“火”,不是指火星,而是一颗恒星,即天蝎座α星,中名“大火”;二十八宿体系建立起来后,又名“心宿二”。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如果纪宝成知道有人迫不及待地用另一个错误来替自己的错误开脱,他是欣慰还是赧颜呢? 文章后面又说什么“学问中人在文字方面、典故理解方面出了纰漏,则足以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让众人踏上一脚,自此遗恨千秋,而在学理、逻辑、创造性方面如果出了差错或毫无建树,则仍可躺在自己的职位上谁大觉,且不用担心遭人家唾骂”,并且以煽情式的口气说,“可怜咱中国人,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醒醒,形成一个全新的评判学问中人的价值体系与标准呢?”作者大概不明白,网民对于纪宝成的专业并不感兴趣,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为本校的国学院摇旗呐喊的校长,本来应该是最懂得宣传之术的,也就应该懂得,在像迎接台湾新党这样的场合,是最不应该出错的;现在不但出了错,还是那么低级的错误,大大损毁了人大国学的形象,连这种宣传之术都玩不好,说他是个不合格的校长,有何不可?何况,纪宝成的校长之位岂是网上的骂声所能撼动的,文章作者如此痛心疾首地反击骂纪宝成的人,简直就是惊弓之鸟。 外国的官员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据几年前的《参考消息》所载,英国的教育内务大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出七乘以八的正确答案,一时引起轰动。可是英国人借此事反思基础教育的力度是否应该加大,中国的一些人却借此事兴奋地说“你看国外都这样!”矫枉过正地批评起中国现行的教育方式来了。现在清华、人大校长相继犯错,网上的骂声还没能推进了真的素质教育的时候,开脱的声音便潮水般冲来。如果说“一个全新的评判学问中人的价值体系与标准”在这种一团和气、照顾大家面子的气氛中——而不是铁面无私、公正透明的气氛中——能建立起来,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我到现在,便进一步明白了中国的学术腐败何以如此猖獗,“学术警察”体制的建立,又何以如此步履维艰。 |
南开大学教授范曾的学识令人遗憾(金仕并) | ||||
作者: 刘夙 | 2005年07月22日11时45分 | | ||||
| ||||
今天在新浪网上看到国际在线的新闻报道《人大校长用错典故遭批评 南开教授称太苛求》(http://news.sina.com.cn/c/2005-07-20/13486484109s.shtml),看到“著名画家、南开大学教授”范曾的“高论”,真是叫人气得想笑。为了替人大校长纪宝成辩护,这位范曾教授甫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半瓶子醋的水平暴露无遗。 范曾说:“有关《诗经》‘七月流火’一语,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中已有确解:‘七月流火’者极言溽夏炎蒸也。流者,下注也;火者,状其炽燃也。”笔者手头恰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界书局缩印阮元刻本,全二册,1997年7月第一版),于是翻检了卷八之一对《七月》一诗的注疏文字,却根本没有找到范曾引用的那段文字。相反,该诗第一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两句的注文如下: 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笺云:大 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将言寒,先著火所在。 在第一章之后的疏中,孔颖达是这么说的: 毛以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备,民奉上命。于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 星也,知是将寒之渐至。 后文又对注文进行了详细的注解,除了将火解释成为“大火(星)”,还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即认为是十二次中的“大火”(按:这个解释是非常牵强的,碍于篇幅,在本文中不赘),但绝无“状其炽燃也”这种解释。 为了保险起见,笔者又检索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版,也没有找到范曾引用的那段话。笔者的朋友帮着查了雒江生先生的《诗经通诂》和程俊英先生的《诗经注译》,也一律将“火”解释为“大火(星)”。至此笔者可以说,即使范引用的那段话,是出自哪本古书,也决不可能是《十三经注疏》里的《诗》孔颖达疏。更可能的是,这根本就是范曾自己的杜撰。 后文范曾又说:“又据郭沫若先生之考,七月指周正七月,实为农历五月,天气转热,而非变凉。”郭沫若在什么著作里做过这样的考证,恕笔者读书不多,一时无法指出,但可以确定的是,认为《七月》中的月份都是周正的,并不是鼎堂先生的原创,在范曾举的《十三经注疏》一书里就有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和诗中描述的物候现象多有不合。如“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如果理解成是“夏历六月收获枣子,八月收获稻米”,那是和常识完全相背的。但如果把这两个月份理解成是夏历月份,那么考虑到今天陕西地区的枣在公历9月成熟,水稻的收割期在公历10月,这两句诗的物候描述就相当准确了。 同样,如果认为“七月流火”的“七月”是夏历五月,更与天文现象不合。因为在三千年前,由于岁差的影响,心宿二(即“大火”星)在夏至之后一个多月才能在傍晚时分显得偏西,这是和夏历七月相符的,而绝不可能提前在周历七月就出现。因此,前人另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即认为《七月》一诗是兼用夏历和周历的。从“四月”至“十月”,都是夏历,从“一之日”至“四之日”,才是周历,“春日”和“蚕月”,则指周历三月,也即夏历正月。这也是目前最通行的解释。 最让人齿冷的是,范曾在后文中又大言不惭地说:“‘豳风’出自奴隶之口唱,必使奴隶而述天象,不亦谬乎?”我不知道范曾有没有把《诗经》完整地读一遍,其中提到星象的诗很多。所以清代大学问家顾炎武才在他的《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除了“七月流火”外,他所举的“三星在天”和“月离于毕”,就分别出自《诗经》中的《唐风·绸缪》、《小雅·渐渐之石》。至于为何“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也很好解释。因为古代生产力低下,历算不发达,人们安排农事和其他生产活动,多倚赖天象定时,所以人人熟知天象,也不足为奇;不仅在古代中国是这样,在其他的古代文明中也是这样。喜欢掉书袋的范曾居然连这种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就侈谈相关的历史问题,中国学界的学风不正又可见一斑。 本来,“七月流火”的词义是不是可以改变,总算还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笔者已撰文主张不能对不合理的语言发展听之任之,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商榷归商榷,岂能用错误来替人大校长纪宝成开脱?笔者另一文曾指出,网上一个署名徐志频的人,以为“七月流火”的“火”是五大行星中的火星,是以错易错,错上加错;谁知道南开教授范曾以错易错的功夫,还在这位徐志频之上,说的几句话,几乎没有一句不错的。范曾似不应做南开的历史学院和文学院教授,做个“胡说八道学院教授”还差不多。 想当年,著名国画家李苦禅之子李燕就曾信口开河地说什么原始人要是没有超凡的预测能力,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他的这一妙论被“易学泰斗”邵伟华视若至宝,在那本“20世纪中国十大伪科学著作”之首的《周易与预测学》中两次引用。由此我开始对中国画家的科学知识不敢恭维。现在看来,连他们的人文知识也是不敢恭维的。可是,李燕起码是清华美院的教授,这和他的特长是符合的;而南开又是凭什么授予一个把历史学成半瓶子醋的画家以历史学院和文学院教授的职务的? 2005.07.21 |
南开大学教授范曾的人品也令人遗憾(金仕并) | ||||
作者: 刘夙 | 2005年07月22日19时07分 | | ||||
| ||||
笔者写作《南开大学教授范曾的学识令人遗憾》一文时,所引用的范曾的原话,是转引自南开新闻网记者的报道(后又被国际在线、新浪网等媒体转载)的。此文写毕,又在网上搜到了范曾替人大校长纪宝成辩护的原文(见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5-7-19/LTD-429335.htm),当即拜读。拜读之后才发现,网上有人说范曾的人品有问题,此言果然不虚。 且看范曾赤裸裸吹捧纪宝成的原文: 纪宝成校長娴于诗旨,不惟无舛,用之甚佳。或有某注家强作解人,必以 “火”为星辰之名,谓“流火”为节候转凉,此胶柱而鼓瑟之谈,则恐非硕学之 宜。且也,“豳风”出自奴隶之口唱,必使奴隶而述天象,不亦谬乎?要之,诗 无达诂,人各有会,期间理解之龃龉,唯不离本文之主旨,正不必刻舟求剑,定 向而解。 如果说,郭沫若夸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是“诗词的顶峰”“书法的顶峰”、钱穆夸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这样的话是“肉麻”的话,则范曾阿谀纪宝成的肉麻程度,又远在郭、钱二人之上了。那么为什么范曾宁要在天下读书人面前出丑也不惜如此阿谀呢?道理很简单,只要看了《北京娱乐信报》今年6月2日的报道《范曾将任教人大国学院》(网易的转载见http://culture.163.com/culture/editor/news/050602/050602_148126.html)就可恍然大悟了: 牐牰杂诰咛褰萄Х桨福纪校长则表示还在制定当中。他说:“《四书五经》这 些内容肯定有,而且教学内容绝不限于儒家,诸子百家以及中国文化发展不同阶 段的经典内容都是教学内容。国学班的定位是当代世界的范围,因此世界历史、 哲学、美学、文艺、科技史等理论方面的东西也在学习之列。此外,我们还聘请 了范曾作为名誉教授,琴棋书画将作为学生的选修课存在。” 一个不过是作为国学班主课的陪衬的选修课的老师,还没有走马上任之时,就对未来的主子大拍马屁,大捧臭脚,怎不令人啧啧称奇!更妙的是,这奴才甚至连主子的意愿都没完全猜透。纪宝成明明说“国学班的定位是当代世界的范围”,所以“世界历史”“科技史”等“理论方面的东西”“也在学习之列”,范曾却说什么“余以为工科硕学不必识篆籀,一若国学大师岂须详欧几里德、高斯”,看来范曾的拍马屁功夫还须再练,目前的水平,也就和前苏联那两位用“无产阶级的爱情和资产阶级的爱情怎能一样”替斯大林的笔误辩护、结果却被斯大林骂为“笨蛋”的教授差不多。 本来,学术批评一般是不应该涉及人品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事例证明,许多学术腐败的产生,是和当事人的人品分不开的。试想如果担任未来的人大国学院的选修课教师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即使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不能公开批评,起码也该保持沉默。也只有像范曾这样人品卑劣的人,才会主动跳出来指鹿为马,倒上为下。有这样的恬不知耻的教授和画家的存在,真是中国学界和画坛的悲哀。 |
刘夙 |
| 笔名诸葛恒、葛民勤等。1982年7月生于山西太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应用化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业余从事科普和科幻小说等的创作。----------------北大狂徒,小屁孩刘夙 |
 加微信,拉你入群
加微信,拉你入群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