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村土地何以成了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话题明显多了起来。从主要关注的角度看,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失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二是农民是否应该获得更大更多土地权利的问题,三是土地规模经营的问题。前两个问题涉及农民的权利,第三个问题涉及农业生产乃至国家粮食安全。都是十分重大的问题。
一, 目前国际粮食价格猛涨,各界都很关心粮食问题,我就先从第三个问题谈起。前不久《农民日报》连续在头版报道湖北种田大户侯安杰在数县种植两万亩土地的新闻,湖北省有关领导批示要重视粮食生产,要给种田大户以实际支持。湖北省是人均耕地很少的省份,竟然有人可以耕种两万亩土地,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新闻。这个种田大户显然不可能自己有这么多的土地,而是向农民租赁的土地,租种时间一般四到五年。期间,种田大户给土地承包户每年每亩定额地租,而将土地出租的农户也可以安心外出务工。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种田大户只有四到五年的租赁土地时间,他没有办法长远安排土地的使用,尤其没有办法建设必要的农业基础设施,比如灌溉体系。两万亩土地,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灌溉设施,是问题多多的。另外,因为是租种不同农户的土地,两万亩土地没有连成片,这不仅影响土地的规模经营,而且也影响土地上的基础设施投资。记者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建议,能否将农户的土地永典给种田大户经营,承包土地的农民因此进城成为市民,种田大户因此成为农场主。经营万亩的农场主多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就上去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生产就有了保障。也因此,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鼓励农民的土地流转,就应该鼓励种田大户的出现。 但是,农民之所以不愿意将土地永典给种田大户,不愿意将土地永久地流转出去,也是有农民自己的考虑。很简单,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收入不足于维持他们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理性考虑的结果是,等到年纪大了,城市务工没有人愿意要了,他们就回来种田。城市务工收入不足以养活进城务工的农民一家人。 在农民的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之前,土地收益都归农民(小农)所有,流转之后就大不同了,就是土地的收益现在归种田大户和一般小农分享。经营大户越多,经营大户种田越多,小农能从农业中分享的收益就越少。并且,种田大户在农业上越是有效率,生产的粮食或者其他农产品越多,一般小农就越是被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也就是说,假定农业收益是一定的话,在没有种田大户出现之前,这些农业收益由全国分散的小农分享。有了种田大户,有了农业资本下乡,之前由小农分享的农业收益,现在不得不先被种田大户切走一大块。分散小农可以从农业中分享的收益减少了。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即使可以提高农业的效率,也不能为一般农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机会。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目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都进城务工的话,除了恶化农民在城市就业的竞争以外,并不能为农民带来更多好处。 从以上算总账的角度可以看到,土地流转给大户经营,至少对一般小农没有好处。种田大户经营的土地越多,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小农从农业上可以得到的总收益就越少。不仅如此,一旦土地永久地流转出去,会带来两个对农民严重不利的后果,一是土地永久流转出去后,农民事实上就不再有机会回到村庄,他们就只能流落到城市。有人说我们正是希望农民进城成为城市人,我们还要制定政策鼓励农民进城呢。但是,农民能否进城并不由农民个人意愿决定,而只能由他们的收入条件决定。前面已经说过,仅靠在城市务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农民在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更别说维持农民在城市的体面生活。他们之前还有农村的家,这个家是他们的信念所在,归宿所在,希望所在。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可以回得去的世外桃源。现在,他们回不去了,只能在城市这个陌生的世界挣扎。尤其重要的是,当农村土地流转不是个别现象,而被政策推动成为普遍现象时,失去家园流落进入城市的农民就不是个别,而是相当规模的现象,这时候,农民在城市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的可能,就会因为相互竞争而进一步减少。 每年春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农民不顾春运拥挤而回家过年,春节尚未结束,大量农民又外出务工的奇特景观。农民工成为候鸟。这当然不好。不过,这总比不允许农民外出务工要好。最好的结果是农民可以不用象候鸟一样城乡两头跑,而是全家搬到城市成为城市市民。但如前所述,依靠现有务工收入,农民全家进城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他们现在是靠了城市务工收入,加上农业收入,而在村庄维持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我们可以将全国大部分农村的农民,看作是兼业的小农。在传统时代,农民往往无法仅仅靠种田来维持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他们不得不从事一些手工业,或者给地主做长工短工来获得部分收入,以维持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目前农民外出务工,就相当于传统时期农民从事手工业等兼业,不同的是,当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比传统时期兼业收入高得多了。且农业收入也比过去高得多了。传统时期的兼业是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农民温饱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他们外出务工是为了维持在农村的体面生活,是有大追求的。在城市务工的收入,相对于城市人也许不多,拿回家乡,这笔收入却可以做点事情。在城市累死累活,农民之所以愿意忍耐,是因为他们对农村的生活抱有期待与希望,他们并不是城里人拼命赚钱拼命消费,而是为未来而积攒。春节太好了,这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的希望。他们要回去再计算一下自己的希望。正是有了希望,农民外出务工才有了意义,有了动力,有了忍受苦难的品格。农村是农民的宗教,是他们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一旦因为土地流转而至大量农民失去村庄的生活,他们在农村的根就没有了,他们长远的期待与希望也就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在城市很难有真正体面生活下来的机会。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他们也就不再有了长远打算,他们为了每天的生活而劳碌奔波。他们不再能够忍受苦难,因为不再具有期待与希望。 将土地永久流转给种田大户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即使有农户愿意将土地永久流转给种田大户,总有农户不愿意。这怎么办?一旦有人不愿意流转,就会使大户的土地不能连成一片,他们的规模经营就不会那么成功。而站在不愿流转土地农户的角度看,当村庄的其他人都将土地流转出去后,他就不得不再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力量(种田大户),即使陌生的种田大户没有恶意,仍然生活在村庄的农民也再难获得之前村庄生活的意义。 从以上讨论来看,假若仅仅从农业上讨论土地规模经营问题,而忽视了现在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数量都极其庞大的农民,这样的农村政策就可能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并因此带来严重后果。 二, 我们再来看看是否应该给农民更多更大土地权利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话分两头来说,一头是土地权利与农业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建设的关系问题,二是哪一部分农民可以从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中受益。 有人认为,站在农民角度,给农民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农民肯定是欢迎的。若你问农民,你要不要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农民肯定会说要。问题是,土地其实是集体的,集体的土地,农民人人有份。更重要的是,土地权利越是明确给农户,土地上的既得利益就越严重,关于土地集体利用(尤其是公共品供给)就越是难以谈判,农民因此就越是可能深受损害。 举例来说,以上湖北省种田大户在土地经营中遇到的基础设施问题,倒是当前农村农业经营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一定三十年不变,虽然土地的所有权是村集体的,但使用权则是农民的,农民人均一亩多耕地,户均不足十亩,这么小的土地面积,就使得农业所需公共品比如灌溉、排涝、机耕道等必须依靠超家庭单位的合作。因为农户具有土地的使用权,公共品建设需要每户农户出钱出力,却可能有人想搭便车。比如,有人的土地就在灌溉渠道的边上,只要渠道流水,他的耕地就可以首先得到灌溉用水,他就可能不愿出钱抽水,而等其他人放水过来,他白得好处。有一户得到好处,其他农户又没有办法将这一农户排挤出去,这一农户的行为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就会出现户户都想搭便车,最终导致公共品供给的失败。 农村的很多公共品都是与土地有关的,要占用土地。因为农户具有土地的使用权,集体想通过调整土地来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就会面临很大困难。农户土地权利越大,调整土地就越是困难,因为每一户农户的利益都不能损害,只要有一户反对,无论调整土地建设公共工程对集体具有多大好处,这样的调整就都没有可能进行。简单地说,因为将集体土地更多权利赋予给了农户,而形成了农户土地上的既得利益刚性,这种既得利益刚性就使得任何对集体有益的变动都变得不再可能。农民土地权利越多越大,超家庭的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公共品供给就越是困难。农户具有越多越大的零碎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就越是不可能依靠集体来获得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品。这是第一个土地权利引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给农民更多更大的土地的权利,是给哪些农民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而可能损害哪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获取的收益。 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法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30年不变,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农民因为小孩考上大学而在城里生活下来,因为外出做生意赚了大钱而在城里买了房子,等等,这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已经从农村转移出去,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他们还有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因此可以以每亩每年300元将土地转包给真正种田的农民。一般来说,可以进城成为真正城里人的家庭,都是相对于在村庄种田农户经济条件要好的比较富裕家庭,这部分比较富裕的家庭凭借30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来向村庄真正种田的比较贫困的家庭收租。而如果集体有较多的土地所有权利,则那些已经进城了的不再真正种地的家庭,理所应当将自己的耕地退出,分配给那些真正种地农户耕种。也就是说,如果集体有比较大的土地权利,本来村里比较穷的农户是不必向那些已经进城的比较富裕的家庭交这笔租的。给农民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实际上可能对真正种田的比较贫困的农民是不利的,而对已经进城了的比较富裕的家庭则是有利的。这样的结果显然有欠正义。 有人认为给农民更多的土地使用权甚至土地所有权,就是将农村土地私有化,农民自然会安排好土地上的公共品。他们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农民会为了土地收益最大化,而交易土地。但是我们知道,用于农作的土地,其农作收益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将土地卖掉,也一定卖不出好价钱(可以计算一下,农民每亩地用于农作的纯收益为400元,即使20年,也才有8000元的纯收益,也就是说,那么若出售土地,每亩市场价格约在万元左右。)这时候,农民就不会贸然将土地卖掉,有人所期望的通过土地买卖来实现土地的永久流转也就没有可能。前述湖北省万亩种田大户,他只能租种农民的土地,即使国家允许土地买卖,这个万亩大户也不会以高于每亩一万元来买地种植粮食。农户显然也不会将自己的土地以低于一万元每亩的价格卖掉。要想让万亩种田大户真正占有大量土地,除非国家制定强制性的土地流转政策。 就是说,只要是用于农作,用于种植大宗的农产品,即使土地私有化,也不能解决土地基础上的公共品供给问题, 李昌平曾说,集体没有任何土地的权利,对于农村是灾难性的。集体没有土地权利,村民自治就没有了经济基础。很简单的道理,村民自治就是由村民就村庄的重大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但是,村集体没有任何资源,村民决策有何用处?村民决策和管理,村民自治,前提是有需要自治的事务和可以自治的权利与资源。现在全国大部分村庄,既没有经济收入又没有土地权利,如何可能谈得上自治? 显然,只要是将土地用于农作,农民并不需要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相反,村集体有一定的土地权利,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和真正种地的农民,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是否所有地方的农民要求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都是虚幻的要求呢?不是。当土地用于非农用途时,土地因其不可移动性,而具有了意义。 三, 何新早就说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在于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国家征地用于城市建设(包括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修建工厂),使我国在大规模城市化时,没有因为土地而影响了经济发展。有一种说法,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农民土地中获得了20万亿的好处,相应地就是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受到20万亿的损失。我以为这种计算是没有依据的。不过,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增值很快,如果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都给到失地(土地被征用)农民,则失地农民将得到巨额好处。有人统计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了数千万失地农民,按20万亿土地利益来计算,每个失地农民应该得到数十万元的好处。 中国目前数千万失地农民并没有得到平均每人数十万元的好处,也不应该得到这个好处,因为土地的增值并非农民努力的结果,而是城市化带来的级差地租。而中国的土地制度,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大部分是农民集体所有,而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土地,则采用征地为国家所有的形式。换句话说,第一,失地农民的土地并非农民私有的土地。第二,即使土地归农民私有,也仅是用于农业生产时归农民私有,而非可以任意改变用途。土地即使私有,土地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也就是说,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化的郊区,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土地的增值,农民如果具有更大更多当土地权利,那么无疑可以增加与国家的谈判能力,从而可以增加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在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农民需要更大更多土地权利,看来是个真问题。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土地增值并非农民努力的结果,因此,即使农民有更大更多土地的权利,土地增值的收益也不应该全部给到农民(有些地区一点都没有给农民也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内地在城市化过程中,尤其是招商引资过程中,牺牲了农民太多的利益)。如果因为土地增值收益给到农民导致大量农民成为城市食利者,则就存在问题了。目前在沿海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农村土地食利阶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无论从土地非农使用中得到多少收益,中国农民中,最多只有5%的农民的土地被非农使用,这部分农民因为邻近大城市或者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就业机会比较多,往往自己盖有比较好的住宅,若说这些人还是农民的话,我们也必须明确,在中国的当前阶段,这些农民已经是十分特殊的农民,已经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农民。我们一定不能以这部分农民的诉求代替了全国95%以上真正农民的诉求。虽然我们都知道,因为存在巨大的土地利益,这5%的农民正在十分积极地上访告状,在毫不妥协地期待从国家的博弈中获得更多利益。借这上访告状的5%的农民的土地诉求来说全国农民的事,是缺少逻辑的。 四,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再次成为问题,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个人以为,如果不能再稍稍增加一点村集体土地的权利的话,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就应该保持目前的这种农民具有相对稳定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制度。我看不出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有何向给农民更多更大权利方向改变的理由。更奇怪的是,一些人竟不顾宪法规定,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农村土地私有化。 2008年5月18日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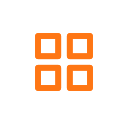 全部版块
全部版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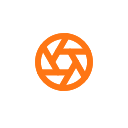 我的主页
我的主页

 收藏
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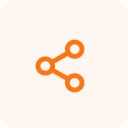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