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朴实的自恋及其所遭受的三次打击
弗洛伊德是个奥地利人,因为所研究的学说距离经济学实在有点远,所以在书店里和图书馆的书架上偶尔看到他的作品时,只是随便翻翻就放下。知道这个人是个名人,坦率的说,我并不知道他的创见在哪里。
在翻阅一本生物学家S.J.古尔德的一本著作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小段引文让我吃惊不小,他揭示了一个真相——
“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得难以想象的宇宙体系中得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得研究剥夺了为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罢黜为动物的后裔。”
而人类的自恋第三次遭受打击是否可以描述为曼德维尔-休谟-弗格森-斯密-哈耶克一路,揭示了那个极为复杂的运转有序的经济系统竟然不是我们理性的结果。在集大成者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和后来的《致命的自负》中,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我们的本能、我们的道德传统、习俗和惯例,我们的理性三者,不过是作为生物的我们在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和不确定的未来过程中形成的一组”适应性办法“,这是”一组”办法,其中我们的理性设计并没有理性自身认为的那么重要和“有智慧”,相反,它本身必须被置于一个“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得框架下得到审视。“我们的理性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指南”这个一向被视为具有高等智能的人类的“理性宣言”看来太过自恋了。伟大人物经常重复的“陈词滥调”——我们的文明取决于文明的行动多大程度上受到理性的指导,看来不过是自恋者的梦呓。哈耶克就是这样一位罢黜了理性在指导我们行动中的绝对优先性的人,他声称——理性只是生物适应性措施中的一种,很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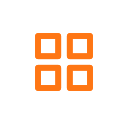 全部版块
全部版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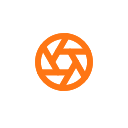 我的主页
我的主页

 收藏
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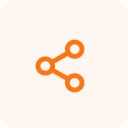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