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7日 09:40 新浪财经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从总产值到GDP:目标调整带动经济高速增长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发展经济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头等大事,因此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应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择方面,也是与时俱进,从50年代初到1987年,在漫长的30多年中我国一直是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反映了我们当初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特征。社会总产值是指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包括饮食业和物资供销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产值之和,也称社会总产品。它与GDP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理论基础不同外,计算的范围和方法也不同。社会总产值是包括物耗在内的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而GDP只是新增加的价值。社会总产值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而GDP则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所以,总产值是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下的评价指标,不仅水分过多,而且忽视了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和科技产业的发展。 因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从198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始,GNP(国民生产总值)终于取代了总产值,也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GNP与GDP之间的差异并不大,GNP等于GDP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素收入(从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支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如国外获得的劳动报酬、投资收益(包括红利、股息和利息等)的净额。但用GDP能够更确切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从1994年开始,政府向人大提交的报告就用GDP这个指标了。采用GDP替代总产值作为考核政府部门业绩的首要目标,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中国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被纳入统计范围内,极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引进外资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中国后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全球最快的,经济规模的的扩大是前30年的4倍左右。 富国还是强民:GDP作为首要目标下的经济不平衡问题日渐严峻 从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每年的人大都要表决通过类似《关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从全国人大到省、市、县的人大都是上行下效地套用这种模式。而自上到下各个行政区域的政府部门每年都无一例外地将经济增长(从过去的总产值到GDP)指标列为首要目标。 尽管各级政府还需要完成如财政预算收入、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环保等诸多指标,但由于GDP是放在首位的,所以是重中之重的目标。而且,从过去30年的GDP这一指标的完成情况看,几乎绝大部分年份都是超额完成的。 过去30年GDP以每年平均9.8%的速度增长,但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却增长缓慢,至今不足美国人均收入的5%。而日本在它高速增长的26年之后,人均收入却超过了美国。虽然我国的收入基数太低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日本和美国劳动者的薪酬总额占GDP比重一般都在60-70%之间,我国则是非常低,据说还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却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在过去30年中,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7个百分点,尤其在1992年经济开始超速增长之后,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9个百分点,增速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城乡收入差距则更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由1990年的2:1左右,扩大到目前的3.3:1。同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最富裕地区和最贫困地区的收入差距达到10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了,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 从“国家”和“国民”之间的财富比例看,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35.48万亿元,07年的利润总额就达到1.76万亿元(截至2007年底国资委的统计),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同时,我国07年末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而同期美国是71%,欧元区是67%,日本是163%。从我国的储蓄率结构看,我国高储蓄率主要是靠企业和政府储蓄率的上升维持的,居民储蓄率这几年是则在缓慢下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居民储蓄的构成,会发现中低收入阶层的储蓄比例是非常低的。 08年颁布的《劳动法》应该是为维护劳动者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大争议,尤其是中小企业和部分外资企业都是税收等来要挟地方政府,而政府往往出于保增长、保税收的压力,更容易偏向后者。因此,把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第一政绩的传统模式,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营造一个让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容易拉大收入差距,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多重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 多年来,我们的发展经济的目标都是多重的,当然,首先是要确保经济增长,如09年提出了GDP保八的目标,其他的目标还有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CPI、节能减排、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促进消费、缩小城乡差距、发展中西部地区等等。尽管所有的这些目标都是基于良好的愿望,也是老百姓翘首以待的,但如前所述,效果并不理想,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都超额完成了,其他指标或者任务却年年欠账。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不妨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0年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作一个贡献因子的相关性分析,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 GDP增长率= 10.47-0.011最终消费贡献(-0.36) GDP增长率= 6.42+0.095资本形成贡献(5.02) GDP增长率= 10.39-0.065净出口贡献(-3.46) 括弧中的数据为t值,从t值看,最终消费贡献是不显著的,可以认为对GDP增速的变化没有明显作用,而资本形成最显著,净出口也是显著的。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GDP增长历来都主要靠投资拉动,当然,94年以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开始加大了。在很多时候,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呈反向关系,GDP增长率高的时候,资本形成的作用就大,消费对GDP的贡献却下降了。 就GDP、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而言,我们发现从04年开始,私营和个体部门已经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体,而到了07年,几乎新增的劳动力都靠个体和私营部门吸纳。而我们4万亿的投资却主要流向公共部门。再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看,也是递减的,从90年代初的120万左右,降到如今只有90万左右了。面对09年面临严酷的就业压力,靠投资拉动的GDP估计最多也只能解决100万新增就业人口,不足全年新增劳动力的十分之一。 1978-2007我国支出法计算的GDP贡献率分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存在很大问题,尽管在过去10多年中自上到下都一致认为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但为何就一直无法实现呢?首先这与我们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有很大关系,其次是忽视了对多重经济目标之间彼此关系的深入分析。 我们之所以在60年漫长的时间内始终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这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遭受外族入侵和欺凌有关,所以“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的教训。而60年来我们经济目标上大同小异,是否与我们政府职能转换相对于经济体制的变化要迟缓有关呢?比如说,一年一度的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作的《关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这样类似的标题已经沿用了50多年(从1957年开始),只是原先只有“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后来又增加了“社会发展计划”。但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我国在积极争取主要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也已经超过50%,这说明中国确实不是计划经济国家了。而且,我国的每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也从原来的“计划”变成了“十一五规划”。既然如此,我们年度的发展目标是否也应该由“计划”变成“规划”,由考核性指标变为参考性指标呢? 对于目标多重化和忽视了对多重经济目标之间彼此关系深入分析的现象,是否与中国长期沿袭思维习惯或文风相关?从古至今,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以辩证逻辑见长,所谓的阴阳平衡。一篇文章犹如一帖中医药方,总要四平八稳,既要怎样,又要怎样,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对非重点又要点到为止,唯恐遗漏,留下话柄。这种思维方式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全面、系统、高瞻远瞩地看问题。缺点就在于不会把文章中提及的各个问题、多个目标通过一组函数模型的方式来表述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节能减排、产业升级与促进就业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彼此的相关系数是多少?国人总是习惯于提倡既要做好这个,又要做好那个,往往是文章写得很好,事情没有做好。关键问题在于一定要深入研究实现目标的可行性,多重目标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扩内需呈反比:是否还要继续把GDP作为首要目标 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觉得启动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二战之后经济起飞和产业升级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发现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而最终消费(也就是我们所提及的扩内需)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比如,在1952至1973年日本经济高达9%的GDP增长期间,日本的消费贡献是65.94%,当GDP增长降低到4.2%的时候,消费的贡献上升近2个百分点,而投资的贡献则下2个多百分点。韩国也是如此,当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比70年代下降10个百分点后,GDP则增加了1个百分点;1998年以后随着消费对GDP的贡献再度提升,GDP增长率则相应下降。而从前面我们对中国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分析也同样发现,消费的贡献率与GDP增长也呈弱负相关。 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及需求构成(%) 年份 GDP 增长率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1952 ~ 1973 年 9.0 65.94 33.48 0.36 1974 ~ 1990 年 4.2 67.78 30.89 1.33 1991 ~ 2000 年 1.5 69.62 28.75 1.6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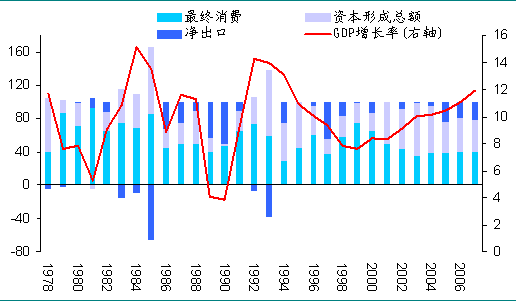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
既然扩内需、保民生与GDP的增长率的提升是负相关,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那就是究竟是要一个鼓舞人气的GDP增长率,还是要提升全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国政府的经济目标,发现大多都选择充分就业、增加失业救济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等目标。而我国由于长期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所以,在财政支出方面,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的比重较大,而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过少,即便是现在有所提高,这还是属于弥补过去的欠债。
中国在过去60年中经济增长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而且,中国的GDP总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也是没有任何悬念,只是时间问题。但如果中国能够让13亿人共同富裕起来,那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所以,现在是到了淡化GDP的时候了,应该把财政支出用在如何更多地提供社会保障,更多地增加就业人数和最大程度上去带动消费方面,而不是用在如何让GDP达到某个增长目标上。而且,中国的行政机构设置的特点都是下级机构仿效上级机构,GDP的目标从中央到县乡都无一例外地成为首要目标,只有中央调整施政目标和职能,地方才会响应。而只有当经济出现萧条、产能大量过剩,失业等社会问题激化的时候,制度改革的时机就来临了。
从总产值到GDP:目标调整带动经济高速增长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发展经济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头等大事,因此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应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择方面,也是与时俱进,从50年代初到1987年,在漫长的30多年中我国一直是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反映了我们当初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特征。社会总产值是指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包括饮食业和物资供销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产值之和,也称社会总产品。它与GDP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理论基础不同外,计算的范围和方法也不同。社会总产值是包括物耗在内的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而GDP只是新增加的价值。社会总产值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而GDP则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所以,总产值是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下的评价指标,不仅水分过多,而且忽视了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和科技产业的发展。
因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从198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始,GNP(国民生产总值)终于取代了总产值,也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GNP与GDP之间的差异并不大,GNP等于GDP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素收入(从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支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如国外获得的劳动报酬、投资收益(包括红利、股息和利息等)的净额。但用GDP能够更确切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从1994年开始,政府向人大提交的报告就用GDP这个指标了。采用GDP替代总产值作为考核政府部门业绩的首要目标,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中国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被纳入统计范围内,极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引进外资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中国后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全球最快的,经济规模的的扩大是前30年的4倍左右。
富国还是强民:GDP作为首要目标下的经济不平衡问题日渐严峻
从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每年的人大都要表决通过类似《关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从全国人大到省、市、县的人大都是上行下效地套用这种模式。而自上到下各个行政区域的政府部门每年都无一例外地将经济增长(从过去的总产值到GDP)指标列为首要目标。 尽管各级政府还需要完成如财政预算收入、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环保等诸多指标,但由于GDP是放在首位的,所以是重中之重的目标。而且,从过去30年的GDP这一指标的完成情况看,几乎绝大部分年份都是超额完成的。
过去30年GDP以每年平均9.8%的速度增长,但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却增长缓慢,至今不足美国人均收入的5%。而日本在它高速增长的26年之后,人均收入却超过了美国。虽然我国的收入基数太低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日本和美国劳动者的薪酬总额占GDP比重一般都在60-70%之间,我国则是非常低,据说还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却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在过去30年中,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7个百分点,尤其在1992年经济开始超速增长之后,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9个百分点,增速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城乡收入差距则更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由1990年的2:1左右,扩大到目前的3.3:1。同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最富裕地区和最贫困地区的收入差距达到10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了,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
从“国家”和“国民”之间的财富比例看,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35.48万亿元,07年的利润总额就达到1.76万亿元(截至2007年底国资委的统计),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同时,我国07年末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而同期美国是71%,欧元区是67%,日本是163%。从我国的储蓄率结构看,我国高储蓄率主要是靠企业和政府储蓄率的上升维持的,居民储蓄率这几年是则在缓慢下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居民储蓄的构成,会发现中低收入阶层的储蓄比例是非常低的。
08年颁布的《劳动法》应该是为维护劳动者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大争议,尤其是中小企业和部分外资企业都是税收等来要挟地方政府,而政府往往出于保增长、保税收的压力,更容易偏向后者。因此,把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第一政绩的传统模式,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营造一个让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容易拉大收入差距,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多重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
多年来,我们的发展经济的目标都是多重的,当然,首先是要确保经济增长,如09年提出了GDP保八的目标,其他的目标还有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CPI、节能减排、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促进消费、缩小城乡差距、发展中西部地区等等。尽管所有的这些目标都是基于良好的愿望,也是老百姓翘首以待的,但如前所述,效果并不理想,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都超额完成了,其他指标或者任务却年年欠账。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不妨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0年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作一个贡献因子的相关性分析,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
GDP增长率= 10.47-0.011最终消费贡献(-0.36)
GDP增长率= 6.42+0.095资本形成贡献(5.02)
GDP增长率= 10.39-0.065净出口贡献(-3.46)
括弧中的数据为t值,从t值看,最终消费贡献是不显著的,可以认为对GDP增速的变化没有明显作用,而资本形成最显著,净出口也是显著的。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GDP增长历来都主要靠投资拉动,当然,94年以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开始加大了。在很多时候,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呈反向关系,GDP增长率高的时候,资本形成的作用就大,消费对GDP的贡献却下降了。
就GDP、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而言,我们发现从04年开始,私营和个体部门已经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体,而到了07年,几乎新增的劳动力都靠个体和私营部门吸纳。而我们4万亿的投资却主要流向公共部门。再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看,也是递减的,从90年代初的120万左右,降到如今只有90万左右了。面对09年面临严酷的就业压力,靠投资拉动的GDP估计最多也只能解决100万新增就业人口,不足全年新增劳动力的十分之一。
1978-2007我国支出法计算的GDP贡献率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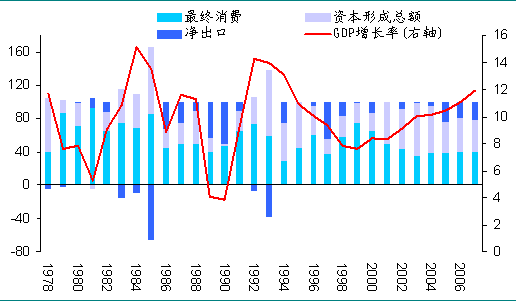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存在很大问题,尽管在过去10多年中自上到下都一致认为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但为何就一直无法实现呢?首先这与我们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有很大关系,其次是忽视了对多重经济目标之间彼此关系的深入分析。
我们之所以在60年漫长的时间内始终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这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遭受外族入侵和欺凌有关,所以“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的教训。而60年来我们经济目标上大同小异,是否与我们政府职能转换相对于经济体制的变化要迟缓有关呢?比如说,一年一度的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作的《关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这样类似的标题已经沿用了50多年(从1957年开始),只是原先只有“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后来又增加了“社会发展计划”。但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我国在积极争取主要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也已经超过50%,这说明中国确实不是计划经济国家了。而且,我国的每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也从原来的“计划”变成了“十一五规划”。既然如此,我们年度的发展目标是否也应该由“计划”变成“规划”,由考核性指标变为参考性指标呢?
对于目标多重化和忽视了对多重经济目标之间彼此关系深入分析的现象,是否与中国长期沿袭思维习惯或文风相关?从古至今,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以辩证逻辑见长,所谓的阴阳平衡。一篇文章犹如一帖中医药方,总要四平八稳,既要怎样,又要怎样,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对非重点又要点到为止,唯恐遗漏,留下话柄。这种思维方式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全面、系统、高瞻远瞩地看问题。缺点就在于不会把文章中提及的各个问题、多个目标通过一组函数模型的方式来表述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节能减排、产业升级与促进就业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彼此的相关系数是多少?国人总是习惯于提倡既要做好这个,又要做好那个,往往是文章写得很好,事情没有做好。关键问题在于一定要深入研究实现目标的可行性,多重目标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扩内需呈反比:是否还要继续把GDP作为首要目标
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觉得启动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二战之后经济起飞和产业升级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发现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而最终消费(也就是我们所提及的扩内需)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比如,在1952至1973年日本经济高达9%的GDP增长期间,日本的消费贡献是65.94%,当GDP增长降低到4.2%的时候,消费的贡献上升近2个百分点,而投资的贡献则下2个多百分点。韩国也是如此,当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比70年代下降10个百分点后,GDP则增加了1个百分点;1998年以后随着消费对GDP的贡献再度提升,GDP增长率则相应下降。而从前面我们对中国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分析也同样发现,消费的贡献率与GDP增长也呈弱负相关。
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及需求构成(%)
年份 | GDP 增长率 | 最终消费 | 资本形成 | 净出口 |
1952 ~ 1973 年 | 9.0 | 65.94 | 33.48 | 0.36 |
1974 ~ 1990 年 | 4.2 | 67.78 | 30.89 | 1.33 |
1991 ~ 2000 年 | 1.5 | 69.62 | 28.75 | 1.64 |
资料来源:IMF
既然扩内需、保民生与GDP的增长率的提升是负相关,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那就是究竟是要一个鼓舞人气的GDP增长率,还是要提升全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国政府的经济目标,发现大多都选择充分就业、增加失业救济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等目标。而我国由于长期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所以,在财政支出方面,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的比重较大,而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过少,即便是现在有所提高,这还是属于弥补过去的欠债。
中国在过去60年中经济增长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而且,中国的GDP总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也是没有任何悬念,只是时间问题。但如果中国能够让13亿人共同富裕起来,那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所以,现在是到了淡化GDP的时候了,应该把财政支出用在如何更多地提供社会保障,更多地增加就业人数和最大程度上去带动消费方面,而不是用在如何让GDP达到某个增长目标上。而且,中国的行政机构设置的特点都是下级机构仿效上级机构,GDP的目标从中央到县乡都无一例外地成为首要目标,只有中央调整施政目标和职能,地方才会响应。而只有当经济出现萧条、产能大量过剩,失业等社会问题激化的时候,制度改革的时机就来临了。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收藏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