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位能给总结一下《佃农理论》的主体思想?特点?
编辑者nie:参见nie在7楼的解释以及牢骚。
[此贴子已经被nie于2006-2-1 10:27:52编辑过]
1、传统理论认为分成租佃会导致佃农的劳动投入达不到社会最优的效率。理由很直观,佃农在边际上每多投入一单位劳动(比如1),就要被地主分享掉部分成果(比如30%),因此这违反了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黄金法则(1>70%)。对税收的分析也是如此。张五常质问:如果固定租金和工资制比分成制更有效率,为什么在许多地方(比如台湾)仍然存在这种分成制呢?张五常在论文中划了那么多线条,就是说明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我看却让很多读者不够明白。
2、张五常的做法是,引入交易费用和风险成本。根据年谨好坏定出一个准确的固定租金或者工资这两种方式也要耗费很多交易费用,重要的是,佃农缺乏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因此,如果存在厘定成本和产出的不确定性,实行分成制可能会提高佃农的效用。这一理论经斯迪格里茨的模型化之后,已经成为今天契约理论中对称信息下存在不确定性的经典模型,这一点张五常居功至伟!斯迪格里茨还引入信息不对称因素。今天我们很容易知道这样一个标准结果:如果信息是不对称的,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那么实行某种分成制就是最佳的。分成比例b=1/(1+r&MC),r表示风险规避程度,&表示方差,MC表示边际成本。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二次方程的结果。
3、我注意到,这里很多网友对一些问题不求甚解,以为弄个半明白就行了,这是不对的。对一些基本原理和经典文献一定要熟稔。我不只一次地强调过,学社会科学,最怕半拉子,还不如不学,要学就要学精。算是共勉吧。
4、补充说一句:青年人要尊重权威,在否定权威之前,麻烦你先弄清楚别人的东西。一些学者早期作出了杰出的成就,后来可能因为人老了,难免说几句夸张的话,但是要把这两者分开。网上的人容易冲动,总是一副“好人不做错事,坏人不做对事”的信念,这是不对的。那些动辄要否定前人权威的人,我看大部分都是螳臂当车。
今天闲来无事逛了一些微观版,发现很多问题没有人解答,只好自己赤膊上阵了。^_^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 10:38:15编辑过]
对一些基本原理和经典文献一定要熟稔。我不只一次地强调过,学社会科学,最怕半拉子,还不如不学,要学就要学精。
聂老师此言让偶倍受教益。

三,交易费用约束下的合约理论
该书第4章,《交易的费用、风险的规避与合约的选择》,尽管被视为代办理论的肇始,但是内容却非常凌乱,作者自己也承认,“我无法将这些零散的分析整合成一个正式的理论:选择理论中涉及交易成本和风险的问题仍是难以克服的。”(第125页)三十年后,作者为本书中文版做序,也只是强调两点:一,风险这个因素可以归纳在交易费用中;二,卸责应是局限下争取最大利益的结果,而且无法判定,不应该单独拿出。(序言,23至26页)
因此对这部分内容的分析比较困难。我并不想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这几十年所有的长足的发展,也无从知晓作者是否有了更有系统性的表述。在这里,我仅就作者在文中的内容做个评述。
在张五常看来,“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使用一个以上的资源所有者的生产资源来提高生产效率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份把这些资源结合起来使用的合约。合约的形成包括以某种形式部分转让产权,例如出租、雇佣或抵押。产权的这种转让,以及在生产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互协调,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其中包括商定和执行合约条款的费用。”(第90至91页)
而合约是可以有各种形式的。之所以存在不同类型的合约安排,至少有两个原因:一、存在自然风险,规避风险有这么几中方法,即搜寻有关未来的信息、投资时选择风险较小的期权交易、把风险分散给其他人;二、由于投入产出的物理属性不同,制度安排不同,不同的合约条款要求在合约的执行与谈判中付出不同的努力,每一种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不同。(第91至92页)
“对于任何一种资源,都会有许多人展开竞争以获得拥有它的权利。……在市场上争夺,所有权的竞争与所有权的可转让性,对合约行为起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93页):对所有资源潜在的所有者来说,竞争汇集了他们的知识;对潜在的合约当事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竞争以及转让使用他的资源权利的能力,降低了执行合约条款的成本。“总之,市场上的竞争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一旦交易成本确定了,合约安排的选择也就确定了。”(第93页)
但是降低交易成本不等于取消了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条件。可是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与帕累托条件一致的资源配置则不一定会使资源利用在边际上相等。”(第94页)这里的边际上的不相等可以划分为两种:
“第一种边际上的不相等可以视为发生在企业间之间,即:相同的要素投入在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用途中会产生不同的边际生产率。例如,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上就不可能有均一的投入要素价格,买方价格可能不同于卖方价格。这种价格差异将导致相同的要素投入在不同的企业中有不同的边际生产率。”(第94页)
“第二种边际上的不相等可以视为发生在企业内部,即: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一个企业所使用的要素的边际产出可能与它的边际要素成本不相一致。”(第94页)例如,如果地主计算用水量很麻烦,成本很高或者甚至根本无法计量,那么,“地主可能只收取固定费用而让佃农自由使用水量。……在这种合约支付形式下,佃农就会使用水资源直到它的边际产出等于零为止,即使水资源的要素边际成本仍为正。”(第95页)当然,如果计量成本小于计量的收入,就会取消这种一次性支付的合约。
“因此,在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有效的资源配置要求每一种资源用在价值较高的选择上。选择的价值可以用效用或财富来度量,因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市场价格。”(第96页)
这就是张五常交易费用约束下的合约选择理论的要点。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理论本身,至于这个理论在地租问题上的应用稍后再谈。
首先,就这个理论本身来说,它要求所有这些合约的签定者都是平等的,是自由的,而且数量上足够多,足以形成竞争。这和张五常的第一个假设是一致的,但是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与他的地租理论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逻辑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他的地租理论所无法避免的。对此,我认为,抛弃他的地租理论,确实是更好的选择。后边我们在讨论他的合约理论在分成地租合约的选择上的应用时,还可以看到这种冲突。这也表明了张五常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思维的不连贯性。
其次,张五常后来声明,风险其实可以归纳在交易费用中,因此不需要单独列出。因此,他的文中所说的“规避风险”的问题,其实可以同样可以解释为减少交易费用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张五常混淆了两种不同的风险。一种是他所探讨的资源配置的交易过程中发生的风险,这种风险确实可以归纳在交易费用中。但是另一种风险,资源配置实现后现实经济运行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引起的风险,却不能归纳为交易成本。当然如果他认为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都可以归结在交易之中,如康芒斯那样,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称为交易,不论是不是资源配置的交易,不论企业内的以及企业外的,那么,这种把“交易”概念无限扩大的做法又有多大的可靠性呢?
事实上,风险本身正是经济活动本身造成的。是为了追逐利润所以才有风险,而不是冒了风险所以才补偿以利润。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依其观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许多派别。所以,张五常自己也非常谨慎的说,“‘规避风险’在这里定义为,在预期平均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宁愿选择较小的风险变化而不是较大的风险变化。”(第99页)其实对于许多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拥护者来说,这都是一个警示,即:如果把“交易”无限扩大的话,首先也要清楚,降低交易费用的意义也是在“预期平均收入相同”的前提下的。抛开收益讲成本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交易费用本身更如同一种“摩擦”,这种费用是经济活动不得不承担的,却不带来任何收入的负担。但是建立在一定的交易方式之上的制度安排,却和经济活动从而和收益直接相关。因此,如果相应的制度安排意味着更多的收益的话,比较多的交易费用当然是可以接受的,直到这种费用超过因此而带来的收入为止,正如张五常自己举的那个佃农用水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
第三,“市场上的竞争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这种说法也是可疑的。我们都知道,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利润的指导下,是通过浪费和失败来实现的。因为,市场本身是没有意志的,市场的作用是通过各种相互悖逆的意志在相当复杂的关系中较量而产生的,这个作用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充斥着失败和浪费的过程。即以张五常所说的资源配置的交易而言,除了寻找“最有价值的选择”本身的交易成本外,其它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的淘汰就意味着其它竞争者努力、资源和时间的浪费。
第四,在张五常随后指出的两种可能存在的与帕累托条件不符的情况中,佃农用水的例子并不能证明他的企业内部边际不相等的可能。因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选择的价值取决于是否存在市场价格。如果地主允许佃农一次性支付后随意使用水,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地主本身不需要再支付用水的费用,这样就没有使用要素的边际成本,一是这种一次性的支付肯定高于佃农使用的量,这样使用要素的边际成本就小于使用该要素的边际产出。如果有第三种可能,即这种一次性支付少于佃农使用的量,就是地主存在其它的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了。
当然这只能说明他举的例子的不妥当,还不能说明他这个边际不相等的可能本身不成立。但是,在一个“企业”(姑且使用这个科斯及其弟子喜欢的用词)内部,正如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所指出的那样,价格机制已经不能起作用了,因此这种边际不相等是再正常不过的可能。与其说这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倒不如说这是“企业”经济计划本身内在的目的使然。
在进一步把这种交易费用约束下的合约选择理论应用于农业的时候,张五常首先说明存在三种合约方式,即定额地租合约,分成合约和工资合约(第96页),“分成合约的总交易成本(谈判成本与实施成本之和),似乎要高于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第97页)。因为分成合约要规定地租的比例,非土地投入对土地的比例,种植的作物种类,还要弄清实际的产量。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分成合约呢?张五常认为,这是为了规避风险(请记住后来张五常已经把风险归纳进交易费用之中),因为分成合约使得地主和佃农分摊了风险。“合约的选择可以用交易成本的不同及规避风险的假设来分析。给定与某一产出相联系的风险状态,较高的交易成本会导致生产性资产的汇报率较低。另一方面,给定交易成本,规避风险则意味着,资产的价值与收入的变化是负相关的。实质上,分成合约下的风险分散会使订约资源的价值较高,而与其相关的较高交易成本则会降低资产的价值。财富的最大化(或取决于相应的度量问题的效用最大化)意味着,所选定的合约安排是能够使订约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合约安排。”(第100页)张五常提出证据,在分成合约应用较多的小麦产区,小麦产出的方差要大大高于分成合约较小采用的南方稻谷产区的稻谷产出的方差。张五常还认为,虽然定额租约可能采用一系列的免责条款来规避风险,但是免责条款的应用使得交易成本过于巨大而变得不合算。所以,虽然“分成合约的交易成本要高于定额租约。所观察到的中国的合约安排表明,一系列免责条款的交易成本要高于分成租约。这是因为,一系列免责条款提供的分散风险的机会要多于分成合约,但据观察只有一种免责条款。因而,合约选择的范围是受交易成本限制的。”(第110页)对张五常的这个观点,我没有任何资料,所以不能提出任何意见。只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张五常又不得不站在了地主的立场之上,要他的地主承担风险就是“强加”的,那么显然让他的佃农承佃风险就是应当的了。这又和他的理论前提直接相矛盾。
回9楼:
1、我不认为引进“风险”是重复的,因为张五常的“交易费用”主要指人为的费用,包括核实产量、讨价还价以及执行费用;而“风险”则主要指非人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比如天灾人祸。尽管张五常自己后来有点后悔,但是他主要是说“风险”难以度量,而非认为风险是多余的。标准的契约理论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技术上用AP风险度量或者效用函数中的风险规避程度来表示“风险”,它与人为的交易费用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同我前面提到的一样。当然,对于风险的测度确实存在困难,也许这方面近年来有一些进展,不过我没有关注。
2、就你举的例子而言,农民缴纳固定公粮,我认为主要与交易费用有关,也与天灾等风险有关,但是与所谓的知识风险没有任何关系。
3、奖励9楼和10楼金钱50、经验30。
<佃农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突破传统,更重要地是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实证了新思想.
我想,对于善于用计量经济学手段的人来说,认真看完张五常的书才会明白什么叫实证.
我很喜欢无常的<蜜蜂的寓言>一文,精巧美观,思想简洁.
回11楼:
我认为经济学研究的“风险”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风险或者由于自然风险的存在从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风险,而不是研究自然风险,比如佃农种地存在自然风险也存在合约风险或交易风险,但是经济学解释的是合约风险或交易风险的问题,自然风险如什么时候下冰雹或者有没有蝗虫灾,以及蝗虫灾对产量有何影响,这都不是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自然风险的存在下,是什么导致或者阻碍了合约的签订,这种影响如何变化,变化以后人的行为是什么。这就是经济学。
其实,合约的标的并不是商品或者劳务而是知识,因为我们发生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有效的知识,所以在合约的缔结中,就要考虑知识的有效性,那么如何度量知识的有效性以及度量的难易都会影响合约的选择方式。所以,选择哪种合约方式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如果签订合约后一方没有知识投入或者虽然有知识投入但投入的知识很容易度量或者投入的知识是免费的,那么就应当采用固定合约;如果合约签订后,双方都有知识投入,但一方投入的知识的有效性很难度量,也就是度量的成本很高,就应当选择分成合约,因为分成合约使度量成本降低了。比如佃农例子中,如果采用的是固定合约,那肯定是地主没有知识投入或者投入的知识或服务是免费的;如果采用的分成合约,那肯定是地主有知识投入或服务,并且这种知识的有效性是很难度量的。
回11楼:
其实,合约的标的并不是商品或者劳务而是知识,因为我们发生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有效的知识,所以在合约的缔结中,就要考虑知识的有效性,那么如何度量知识的有效性以及度量的难易都会影响合约的选择方式。所以,选择哪种合约方式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如果签订合约后一方没有知识投入或者虽然有知识投入但投入的知识很容易度量或者投入的知识是免费的,那么就应当采用固定合约;如果合约签订后,双方都有知识投入,但一方投入的知识的有效性很难度量,也就是度量的成本很高,就应当选择分成合约,因为分成合约使度量成本降低了。比如佃农例子中,如果采用的是固定合约,那肯定是地主没有知识投入或者投入的知识或服务是免费的;如果采用的分成合约,那肯定是地主有知识投入或服务,并且这种知识的有效性是很难度量的。
建议你找任何一本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的教材看一下,再结合你自己的分析。不能先入为主地用自己的理解替代现有的成熟理论。比如说,委托代理理论基本上都假定委托人不参与生产,因此你说的地主的知识投入在模型中通常不存在。
回14楼:
我觉得你把知识投入与具体生产投入搞混了,我们说在市场经济中,生产是为了交易,所以将生产与交易孤立起来的分析是不科学的,交易往往已经包含了生产,所以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是一种知识交易而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交易,这样委托人与代理人都有知识投入,否则交易是不会存在的,当然委托人可能不参加生产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委托人没有知识投入。
下面我借鉴一下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中第五章的一道习题来加以说明:“在公司制企业中,股东、经理、债权人、工人、顾客、供货商等都被称为“利益相关者”。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特别地,解释在什么意义可以说“工人是委托人,经理是代理人”?
在这道题中我只想借用两种关系来说明我地观点,第一,工人与经理的关系。不论是工人委托经理还是经理委托工人,双方都有知识投入。第二,股东与经理或工人之间的关系。经理与工人的知识投入很容易理解,股东的知识投入也比较明显,如公司的发展方向、发展规模以及一些制度设计,还有监督都是或存在股东的知识投入。
注:我的目的不是回答这道题而是说明我有关合约选择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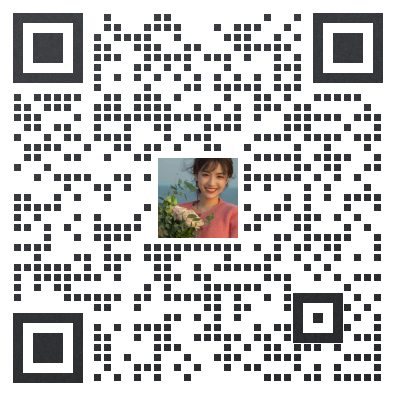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收藏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