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应为中国经济学的解困做出贡献
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20周年笔谈(5)
武 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100836)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一、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中国经济学的困惑早就存在了,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6年里,一是通过开放式的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缓解和掩盖了这种危机;二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或曰“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也似乎并不十分需要某种经济学理论的事先指导,而是通过国内外的经验所获得的创新。而当中国市场经济框架一旦建立,当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展到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产生矛盾甚至冲突时,也即中国的经济改革帕累托最优(人人受益)消失后,中国的经济学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回答经济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不仅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常常左右依违,不得要领。因此,作为显学,最近几年经济学和不少经济学家遭到了社会大众的责难和诟病。
古人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回顾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与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就会发现,经济学的困惑实际上是来自两个方面的。第一,从客观上看,新中国这56年来的经济体制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走了一个巨大的“之”字形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消灭旧中国官僚资本和地主经济为主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到建立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再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直至今天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几次带有革命性的剧烈的体制变动,时至今日尚未完成,这就使经济学的规范研究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从主观上看,由于经济体制始终处于剧烈变动的过程,再加上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大力推进工业化的要求,建国以来的经济学是在一种基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引进建立和发展起来的:50年代为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大规模学习和引进苏联的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80年代以后为了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是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但是,这两次大规模的、带有对先前经济学颠覆性的引进,使得中国经济学在50多年里更多地是发挥了原有知识、理论的传播和普及作用,即“二传手”的作用。换句话来说,经济学界是端来了“一碗饭”,至于好吃不好吃,是否对中国的胃口,更多地是需要决策者和老百姓自己去品尝和摸索。这才是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决策者并不十分看重经济学家,老百姓对经济学家不满意的根本所在。
二、经济学遭遇挑战的原因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的经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活跃时期。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1991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经验的总结,通过吸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通过吸收西方经济学、亚洲“四小龙”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理论,试图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个时期,引领经济学界的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运行都非常熟悉的经济学家。
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集大成者可以反映在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实际上,上述提法正如当时有些学者所说,距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差一层窗户纸了。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终于一锤定音,随后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今后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包括了其基础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此经济学界也打破了一段时间的沉闷和长期受到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惑,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虽然经过l5年的探索,从理论上解决了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地位,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问题,以及实际上的分配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问题:即没有从根本上回答清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一般的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因此,虽然经过20多年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显得苍白无力,不能形成一套令人满意的解释现行经济现象和规范未来发展的完整体系。当然,这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既具有特殊性,又正处于转型期,还没有尘埃落定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释和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改良的局面自然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当思想禁锢被打破以后,“开眼看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引进外国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就成为经济学界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此时外国的经济学在战后的30年里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体制和发展阶段的相近,一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成为学习和介绍的热点,其中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成为解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理论。二是发展经济学成为热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到l992年以后,当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确定不移的改革方向以后,产生和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则又转而成为人们学习和引进的热点。在此期间,90年代前期以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研究对象的“过渡经济学”曾经引起人们的关注;90年代后期为适应国有经济改革需要的“产权理论”和公司理论成为显学;新世纪以来为适应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而使哈耶克、布坎南炙手可热,都反映出当我们自己的理论不能解释自己的现象时,引进和借用外国的理论就成为必然的现象。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怎样学习和借鉴。
经过26年的“饥不择食”的引进,我们应该进入一个以消化和吸收为主的阶段,当一般经济学知识和理论成为常识以后,更重要的如何是将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能够科学解释和指导中国实际的新理论。但是,由于这种吸收和消化需假以时日,需要做认真艰苦的实证研究,即需要花费大的力气,而这一点又是现在的科研体制和社会转型期所忽视的,这就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新观点、新理论的引进和炒作热潮,一轮又一轮的肤浅批评浪潮或廉价的颂扬浪潮。由此造成近年来社会大众对经济学界的普遍不满。
三、经济史学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在经济学界所出现的不少肤浅观点和谬误,有些是来自对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的一知半解。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大量地、主要地、如饥似渴地从国外的经济学中吸取知识和理论时,怎样将其应用于中国并有所创新时,就愈加需要中国经济史这块基石了。
首先,应该明确经济史的定位:它是经济学的“源泉”之一,而不是经济学的“支流”之一。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是这个常识还不普及。就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来说,仅仅学习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要求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资源禀赋、国家统一、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环境以及目前所处阶段等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始终存在一个西方经济学如何“中国化”的任务,即如何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并进而总结中国的经验,为经济学科发展做出贡献。基于这个长期的、基本的任务,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中把握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就自然成为经济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基础部分。
第二,是经济学应该通古今之变。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165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且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各种各样的内外因素制约,转型是艰难和曲折的。如果细分,其中还可以大致划分为几个小的转型阶段:(1)1840—1911年为第一个阶段。其特点是在基本保持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和市场化;(2)1911—1949为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想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和工业化;(3)1949—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是通过革命建立起强大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体制和实行非均衡赶超发展战略;(4)1978—2005年为第四个阶段,其特点是通过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从以上连续不断递进的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仅长期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基本因素,诸如人口、资源禀赋、外部环境、思想文化等变化,需要从整个转型期去分析和研究,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诸如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和社区组织、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等等,也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认识和研究。否则很难得到准确全面的认识和有效的对策。我们不要因为缺乏历史经验而重复前人的教训。
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前人给定的条件和环境中去改革、去发展。同样,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为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正确依据的经济理论,也只能建立在充分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因此,无论是经济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如果有厚实的经济史研究作为基础,如果对中国56年来甚至更远的历史及其遗产作深入细致的研究,相信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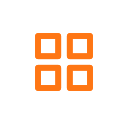 全部版块
全部版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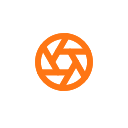 我的主页
我的主页

 收藏
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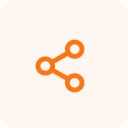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